New Articles
-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2026/02/24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2026/02/24【共生经济学·前言】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The Cognitive Bias and Fragmentation of Economics as...
-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2026/02/22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2026/02/22《共生经济学》自序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How Should We Face the “Ultimate Free Lunch”? 一、从宇...
-
 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2026/02/17
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2026/02/17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Modern National Normalization under the Global Symbiotic Paradigm ...
-
 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2026/02/16
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2026/02/16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Chinese Reproductive Officialdom: Why Regime Change Has Not...
共生思想理论前沿
THE THEORY
-

-

-

-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Symbiosism:Charles Thomas Taylor &Qian hong又一次量子缠绕...
查看详细说明
Speech
-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 ——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钱 宏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语从金音玉(Yǜ):金口玉言,一诺千金,性人诚恳、执信; &n...
-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点击播放 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访钱宏主持人:...
共生的哲学:从“自我”到“他人”
摘 要:共生的哲学视野要求共生体制下的人们抛弃“自我”的个性 、利益张扬,取而代之,以“我们”一体化的语境,乃至“他人”优先的人生观、价值观。尊重他人的“自我”,才有真正的共生。
关键字:共生;我们;自我;他人
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有“我们”、“自我”和“他人”三种观念;每个人也都会言说“我”、“我们”和“他”。但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个人心目中,三者所占的地位各不相同。中华传统文化以“我们”优先,个人所着重于其自身的,是其所处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即 “身份”;西方传统文化以“自我”优先,个人所着重于其自身的,是其不同于群体的独特性、个性1 ;西方现当代文化,一反传统,批判个人主义,重视他人。
一、西方传统文化:从“我们”优先到“自我”优先
西方传统文化,从前苏格拉底到近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尔以至黑格尔哲学,是一个从“我们”优先到“自我”优先、以至吹胀“自我”的过程。
古希腊思想文化中,独立的个体性自我,或湮没于宇宙整体的必然性之内,或湮没于社会群体之内,而没有突显出来。柏拉图关于“不可见”的“善”的理念“超越存在之上”的思想,按照犹太裔法国现代哲学家莱维纳斯的说法,包含有重“他者”的思想因素。2 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容许了自由意志的空间,但独立的个体性自我在中世纪受到了封建教会的压制。西方自我意识的觉醒,主要开始于文艺复兴;后经宗教改革、18世纪的启蒙运动,独立的个体性自我才代替上帝而成为世界万物之主。霍布斯的个人主义由此而在西方近代社会中占有了主导地位。 笛卡尔把“自我”视为一种“实体”,使“自我”落入了不自主的现象领域,失去了统摄知识的功能。笛卡尔在突显“自我”的同时,又认为“无限”――上帝的观念才是最完满的,隐含重视“他者”的思想因素。3 尽管如此,笛卡尔和柏拉图并没有把“善”和“无限”的观念落实到社会现实中,从而像希伯莱文化那样,让“他者”占优先地位,以“无限”的完满性和“至善”来衡量“自我”。康德的“先验自我”观否定了笛卡尔的“自我”的实体性,而强调了“自我”的非实体性,使“自我”有了统摄知识的功能;康德的自律意志,只根据自我的理性行事,而又独立于经验世界,这一观点既把康德的“自我”推到了更加独立自主的地位,又使道德含有“他者”的思想因素。不过无论如何,康德认为,尊重他人源于尊重人类共同的理性,尊重他人即尊重自我,而非尊重他人之“他性”。所以康德的道德哲学,归根到底,仍然是以“自我”占优先地位。黑格尔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他的客观唯心主义把“自我”吹胀到了“绝对主体”、“绝对精神”的地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不断克服与“自我”对立的“他者”而达到绝对同一的“绝对主体”、“绝对精神”的过程;他在关于“自我意识”及其初级阶段“欲望”的分析中,还明白强调“自我”的“自我性”在于“自我”与“他人”间的“相互承认”。黑格尔哲学既是西方哲学史上最系统讲述“他者”、“他人”的重要地位的体系(没有对“他者”的对立性的漫长曲折的克服过程,就没有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又是一个最系统地同化、统摄和压抑“他者”的体系。归根结底,作为西方传统哲学之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其哲学乃是自我哲学的最大代表。在他那里,“自我”最终吞噬了“他人”,成了唯我独尊的独裁者。美国当代学者Robert C.Solomon把黑格尔对“自我”的吹胀,称为“先验的自负”,它把人吹得“多于人性”,“视自我为绝对精神”,这就“无异于把自我看成什么也不是”。4
二、西方现当代文化中由“自我”优先到“他人”优先的转折
黑格尔死后,他的“绝对主体”垮台了,主体性哲学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遭到批判,“自我”的霸权日渐消失。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欧洲大陆哲学的主流主张主客融合,重视他人。
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学说仍然继承了笛卡尔、康德以来的主体性哲学的思路,但他的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先验自我”学说所包含的唯我独尊的弊端:“自我”成了没有“他人”的孤独者。为了避免这种弊端,他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关于“相互承认”的观点,提出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理论,意图走出“自我”,面对“他人”,避免了把他人还原为自我意识现象的唯我论。5 标志着西方哲学由自我优先到他人优先的转折。
海德格尔比胡塞尔更鲜明,他认为,人与世界的融合先于“主-客”关系,自我与他人的“共在”先于自我。自我并非首先是先验的、纯粹的,而是一向在世界中的,一向与他人不可分离的。“一个无世界的单纯的主体决不最先‘存在’”,“一个无他人的孤立的‘我’归根结底也远非首先存在”。 6总之,在胡塞尔那里,他人的独立性、异己性是从自我的“同感”出发而获得其意义,以自我的“同感”为基础;在海德格尔那里,他人的独立性、异己性从一开始就是与自我“共在”的。海德格尔关于“他者”的观点与论证比胡塞尔前进了一大步。
三、“他人”优先反对“自我”优先
如果说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观点还只是标志着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由“自我”优先到“他人”优先的某种转折,从而仍带有“自我”优先的传统印迹,那么,奥地利的犹太哲学家布伯(M.Buber,1878-1965)和莱维纳斯则代表着希伯莱文化传统以“他人”占优先地位的思想特点。
布伯关于“我-它”与“我-你”两种人生关系的学说,表明了自我对他者的两种態度:前者是把世界万物(包括他人)当作使用对象的態度,后者是把世界万物(包括他人)看作与自我同样具有主体性的自我的態度。不过布伯作为一个犹太宗教家,认为“我-你”关系是人与上帝的关系的体现,“你”-“他人”具有上帝的神性,犹太人就是以“你”来称呼上帝的,以“我”为主,把他人、他物只看成是对象而生活的人,只能生活在过眼云烟中。6
与布伯不同,另一位犹太哲学家莱维纳斯,为了进一步突显“他人”的优先地位,强调其独立性、异己性,主张上帝不是遍在的,而是“他者”(The other),是我和你之外的第三者;布伯的“你”并没有讲出上帝的“他性”,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他人”。“他人”是“无限观念的具体化”,“无限”通过“他人”而显示自己。在布伯那里,我与他人相互回应,这种“相互性”表明布伯尚未突出“他人”的优先权;而在莱维纳斯看来,我与他人不是对称平衡的相互关系:在上帝面前,我对他人负有责任,我听从他人的命令,我回应他人,而不是他人回应我。我是被动的,他人是主动的。他人比自我重要,我对他人负有责任,这责任源自超越自然、超越存在之外的力量,而非源于“自我”、“存在”的本性。这就彻底否定了西方传统哲学之以自我为主体、以他人为被动物件的专制暴政,彻底推翻了自我对他人的霸权。7
总之,西方传统文化尽管有像柏拉图的“善”的理念,笛卡尔的“无限”观念,康德所设定的上帝理念等等超验性、外在性的观点,但在莱维纳斯心目中,似乎都被内在性掩盖了。内在性优于和高于外在性,这就是西方传统文化以“自我”占优先地位而不尊重“他人”的思想根源。作为希伯莱文化传统继承人的犹太哲学家莱维纳斯,正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大肆张扬外在性,以达到“他人”优先于“自我”的目的。
四、尊重他人的“自我”,才有真正的共生
人生之初不分主客,没有自我意识,其去禽兽也几希,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人。只有成长到有了自我意识,能区分主与客,这才算得是一个脱离了动物状態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一个由“我们”优先到“自我”优先的转化过程。个人从出生到能有自我意识,说出“我”字,其所需时间,大约只需两、三年;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由“我们”优先到“自我”优先,则往往以百年计或千年计。西方传统文化发展的步伐比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步伐要快,前者的“自我”优先阶段较长,而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处在大力召唤“自我”觉醒的阶段: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由于长期以“我们”优先,压抑个体性的“自我”,因此比起西方文化来也就更谈不上“尊重”“他人”的问题。
“他人”与亲人相对而言,有外人之意。 此种外人-他人所受到的压力源自“我们”的专制主义。以“我们”优先的文化传统在中国文人中所形成的一种“一唱亿和”的千年顽症,此顽症的弊端是不能让个体性自我表达己见。
第二,中华传统文化当然也不乏“自我”的观念,但中国人“自我”观念的内涵大不同于西方。
西方人的自我,是“独立型自我”,指独立的个体性自我,其内涵仅包含此自我一人;中国人的自我,是“互倚型自我”,其内涵包括我的父母、家人,以至于至亲好友。故中国人说“我”,往往实指某种范围的社会群体的“我们”。 把“自我”湮没于“我们”之中,无视“自我”,陷“他人”于无基本人权的境地,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我们专制主义”的一种表现和弊病。
第三,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和弊病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尚未达到自我觉醒、突显自我的阶段,也就不可能达到尊重他人的阶段。
所谓尊重他人,其核心内涵应是指尊重他人的“自我性”。“自我性”,就是指每个个人的自由意志、独立自主性和独创性,这是每个人之为人的本质之所在,每个人的尊严之所在。我尊重他人,就是指尊重他人的“自我性”。这样,尊重“他性”与尊重“自我性”便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的。
五、共生在中华传统下的可能性
中华传统文化未来的发展道路应该是:以固有的万有息息相通的一体思想为基础,吸取西方近代重自我的独创精神,从“我们”中突显“自我”的地位,同时,也吸取希伯莱文化的优点,防止吹胀自我,注意尊重他人的“异己性”(“他性”),以达到“和而不同”的理想局面。“和而不同”是儒家的古训,当前人们也已把它变成老生常谈。但在中华大帝国长期封建统治的历史背景下,谈“和”则可,谈“不同”则多令人生畏;随声附和,仍为时尚;听不进不同的声音,看不惯不同的面孔;否则,就是妨碍“统一”,妨碍“和谐”。其实,针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真正地,切实地做到尊重“不同”,尊重“他性”(他人的“自我性”),才有真正的、切实的(而不是表面的)“共生”。
—————————
1张世英:《“我”和“我们”》,载《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2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27页。
3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29页
4Robert C,Solomon,Continental Philosophy Since 17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202
5Edmund Husserl,Gesammelte Schriften 8, Felix Meiner Verlag,1992,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S,150-S.153
6M.Heidegger,Being And Time,SCM Press LTD,1962,P,152
7M.Buber,I and Thou, English Edition by Charles Scribner’s,1958,P.12-13
8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41,154,216,222,225,230页。
作者:张世英,当代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全球共生研究院高级顾问,本文是作者特为在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撰写的文章,时年94岁。
上一篇: 如何共生?
下一篇: 共生的本体生態学: 易道而共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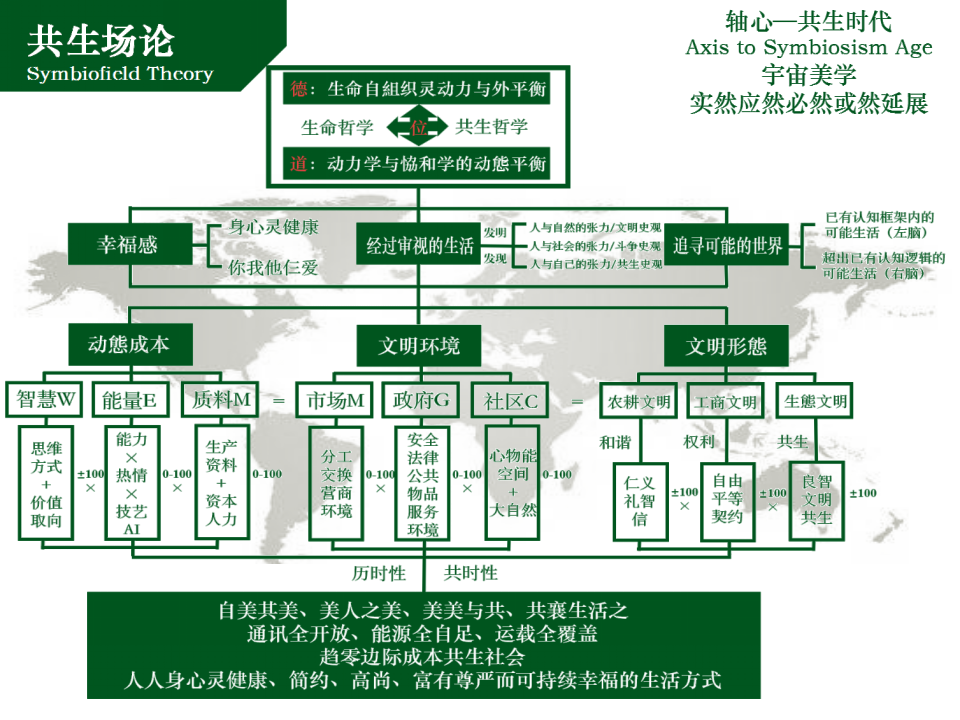





您好!请登录
已有0评论
购物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