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Articles
-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2026/02/24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2026/02/24【共生经济学·前言】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The Cognitive Bias and Fragmentation of Economics as...
-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2026/02/22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2026/02/22《共生经济学》自序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How Should We Face the “Ultimate Free Lunch”? 一、从宇...
-
 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2026/02/17
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2026/02/17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Modern National Normalization under the Global Symbiotic Paradigm ...
-
 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2026/02/16
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2026/02/16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Chinese Reproductive Officialdom: Why Regime Change Has Not...
共生思想理论前沿
THE THEORY
-

-

-

-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Symbiosism:Charles Thomas Taylor &Qian hong又一次量子缠绕...
查看详细说明
Speech
-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 ——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钱 宏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语从金音玉(Yǜ):金口玉言,一诺千金,性人诚恳、执信; &n...
-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点击播放 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访钱宏主持人:...
为何国内学者的理论思维含量如此之低
为何国内学者的理论思维含量如此之低
原题为《读〈读黑格尔〉所感》
提要与简评:
“历史与逻辑的同一”只是一种理论信念而非事实判断,只是一种理想境界而非生活现实。中国人错认后者为前者,往往不顾实际强求事实与理论的统一。
而中国人习惯于述而不作的学术研究传统,缺少西方理论思维的训练,这进一步造成了中国的思想理论只能达到“现象的描述”水平,理论思维含量很低。
此文批评了国内学者轻视理论思维训练的现象,主张尽早实现中国式的学术研究与西式的理论思维的联姻。
王元化先生大鉴:
刚拿到先生的大作——《读黑格尔》时,特约编辑刘景琳(也是我的朋友)就来电要我为先生的大作写一篇评论性文字,我回答他说:还在80年代初,我就读过王先生的《文学沉思录》,后来又有幸在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拜见过王先生,对王先生的为人和文章我一直非常敬佩,所以,虽不敢说写评论文字,但写点学习心得或感想还是可以的。可当时忙于《国学大师丛书》的评奖工作(这是组织派下的任务),这事就耽搁下来了。
最近稍暇,始得以拜读先生大作,昨日又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许纪霖先生的评论文章,遂想起该兑现自己的诺言了,可是提起笔来又顿感涩得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动过笔了),于是就想到给先生写信求教,顺便把我的一些零星的感想带出来。
关于先生对中国现当代学术思潮的反思与先生的自我解剖精神及大作的内容,这里我就不打算多说了(人微言轻,赞美或反对都不重要)。我这儿主要是把我在读《读黑格尔》后所触发的几点感慨说出来,就教先生。
中国人了解黑格尔,除极少的几位大师级人物,大抵是通过恩格斯、列宁、艾思奇(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还通过马克思及普列汉洛夫)的权威“捷径”实现的。这就难免留有两大缺憾,一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为得之于“二手货”);二是只会“照着说”“套着用”,不会追问和扬弃(因为得之于“权威”)。
结果,出了问题就要么陷迷惑、不知所措,要么走极端、怀疑动摇。
一、在理论思维(包括知性和理性两个环节)中,“历史的与逻辑的同一”属于“从概念系列(理论图景或模型)中再现具体”的理性思维范畴,也是爱因斯坦经常说的创造性思维中的“思想实验”’的依据(信念)之一。因此,历史的与逻辑的同一,既不是先验的产物,也不能从知性概念(来自常识、经验、知识及现成理论概念的归纳)中逻辑地推演出来,更不能作为理论公式到生活现实中去套用。
二、因此,所谓“历史的与逻辑的同一”(或“实际的与真际的同一”、“生活的与艺术的同一”),只是一种理论信念而非事实判断,是一种理想境界而非生活现实。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错认后者为前者。这样才会忽视所谓的“知性思维”并把“理性思维”贬低到“知性”水平(知性“不能掌握美”,所以中国人一说到“理性”总是立马一脸正经不苟言笑;李泽厚使用过的“实用理性”一词,或可玩味)。把“逻辑的”当成“历史的”,或把“历史的”当成“逻辑的”并认为其简单同一,是典型的“知性思维”。而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不顾实际,强求事实与理论统一,当然会犯“盲动主义”(非主观主义、亦非唯心主义!);而忽视理论尤其是理论精神,只知“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就会陷入“被动主义”(非客观主义、亦非唯物主义)。
三、坚持某种理论信念,当然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所有理论都有一个共同克星,即斯宾诺莎原理——“规定就是否定”(排除既有的、遏制新生的),但是,所有理论风险都与一定的实际回报相联系。至于那“回报”值不值,值多少,则既非逻辑判断也非事实判断的范畴了。
四、恩格斯的确在不同场合一方面极力强调“一个民族”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另一方面又指控过“青年人”动辄构造一个理论体系。可我们中国的学者们极易偏向带指控性的后者,却乐得只把前者当作一句漂亮的口号或辞藻,似乎压根儿没打算实施过——因为理论思维或理论创造往往“吃力不讨好’”,假若你手中没有“首创权”还有可能因“思想”而入“文字狱”累及亲友后代(孔老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傻子精神不再);而我们习惯了的“述而不作”的学术“研究”传统,虽然有限,但的确“很实在”、有“收成”,而且基本上不带什么“风险”。如果把中国人重现世人生,因而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异常敏感这一点考虑在内,就更容易理解何以至此!
五、我们中国人以后者取代前者(最好的情况是所谓“活用”“化用”或曰“理论联系实际”)而不自知,出了问题就动摇其“信念”,结果要么走向“理论取消主义”,要么陷入“一地鸡毛”式的“争鸣”、“论战”或“清谈”——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过于容易是理论精神的脆弱。记得1983年秋天,我曾为参加1984 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思维科学研讨会”,冒昧地写过一篇题为《谈谈理论思维的内部机制》的小文章,可在会上得到的反应是听起来很“辩证”很“平稳”的:这种探讨是否能得到自然科学的证实还不好说(这是中国式极端的另一种形式)。所以,尽管该文后来在当时的《国内哲学动态》(1985年第8期)刊出,我对它有何效果根本就没抱任何指望。
六、如今,我依然斗胆以为,我们中国人要想雄健地自立于未来世界,就应尽早实行中国式的学术研究与西式理论思维的联姻(不必理会“古已有之论”者)。为此,我想也许我们中国的学者,还必须首先自觉强化一下理论思维的训练(包括“二律背反”、“形而上学”、“思想实验”和基本逻辑等等。“历史的与逻辑的同一”是其中的一个“子项”)。我们中国人往往为太多的“常识”所惑,而甘愿停滞在理论思维的“槛外”自我陶醉——即使学富如钟书老人,其《管锥编》《谈艺录》可谓金光四射叫人开卷必有所得的鸿篇大著,掩卷之下,仍旧让人留下未凌“绝顶”的遗憾……我种过十一年田,进入80年代以来,每每生发出这样的联想:没有“理论思维训练”的学者,其工作,在本质上与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勤劳的“老农夫”何异?……
七、由此,又联想到一种席卷当今学界的所谓“务实精神”——我指的是那种“占领性”地宣布自己是“专治”某某学、“专搞”某某史、“专吃”某某饭或“关注”某某人、某某领域的“时尚”(这种时尚,很容易让人想起“跑马圈地”的故事)。这种时尚的形成,一是学界对80年代以前全民族空想式的机械“应用”及之后且延至90年代前期的“宣言式的创造”(表现为食洋不化的“引进风”或食古不化的“复兴风”)的反动,二是我国研究生培养走向专才(非通才)化、规范(弃博从约)化教育和各类“技术职务”评定的条件化、阶梯化、待遇化运作的当然后果。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本无可厚非,而且它的确可能造就一批批可称道的“专家”;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它还将导致——尤其近年来在西方所谓“话语权力”及“新历史主义”理论的鞭策下——中国学界走向一种社会金字塔式(各得其所)的“学术割据”(类“政治割据”、“军事割据”)和“学术垄断”(类“垄断经营”、“占市场份额”)的境地。
八、由于这种“割据”与“垄断”势必在整体上陷我国思想理论于“现象的描述”水平而难以自拔,中国学界的“学术研究成果”与“理论思维含量”,虽不说会呈反比例发展,要说会呈正比例发展则恐怕很难。当一个民族的学界人士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社会金字塔的阶梯,而且还受到某种“理论”(从“教化或启蒙理论”到“科学理论”再到“话语权力理论”不绝于耳)及“现实生存需要”的鼓舞时,那种面对“青灯古佛”、“宇宙洪荒”、更需“大悲大悯”、“无为而为”情怀(吃力不讨好)的“理论思维”怎么还会有人光顾呢?——然而,若非“圣子”、“真人”、“活佛”,抢着“话筒”更有何益?反之,“话筒”何需抢(“地皮”何需圈)?斯宾诺莎是个磨镜片的,康德哲学诞生于他当私人教师时期(1746—1755),黑格尔30岁前和年轻的谢林教授通信时也只是个家庭教师,马克思一生都在贫困中度过,福柯拿到“科学史”博士文凭后很久仍没有被哲学界真正接受……
此外,我以为,假若没有“佛学”——东方智慧中“理论思维含量”最高的一种学说——的浸润,我们中国人就读不到像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一成“体系”(起码是“准体系”)的——千古一书!
不当之处,诚请先生明示为盼。
如果可能的话,作为一名普通编辑(大概我命里注定可以“为他人作嫁衣”吧),我很希望为先生编印《读刘勰》,以作为《读黑格尔》的姐妹篇,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余容后叙,顺致
崇高的敬意!
晚辈: 钱 宏 顿首
丁丑年十一月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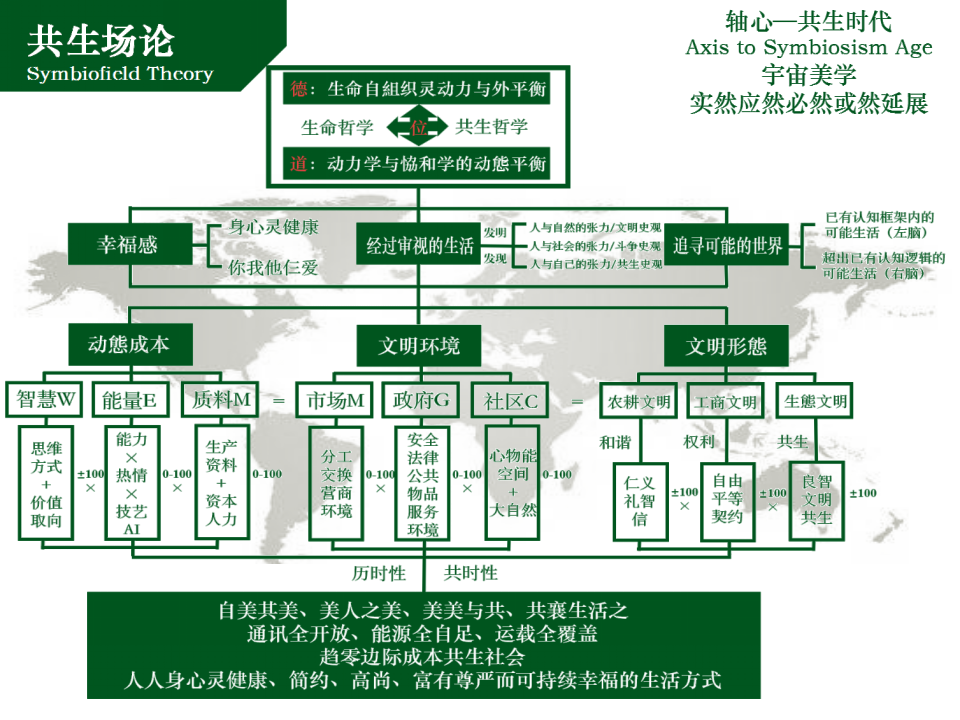





您好!请登录
已有0评论
购物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