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Articles
-
 AI三大瓶颈及其10个“傻白”和5个“傻精” 2026/02/04
AI三大瓶颈及其10个“傻白”和5个“傻精” 2026/02/04AI三大瓶颈及其10个“傻白”和5个“傻精”The Three Major Bottlenecks of AI and Its “10 Naïve Blind Spots” and “5 Cunnin...
-
 共生场图灵测试 (SFTT)的设计 2026/02/03
共生场图灵测试 (SFTT)的设计 2026/02/03共生场图灵测试 (SFTT)的设计Symbiotic Field Turing Test (SFTT) Design 本报告根据Google AI与Archer宏2...
-
 沃什、马斯克与钱宏 GDE 体系:把握宏观不确... 2026/02/02
沃什、马斯克与钱宏 GDE 体系:把握宏观不确... 2026/02/02沃什、马斯克与钱宏 GDE 体系:把握宏观不确定性的范式革命 Warsh, Musk, and Hong Qian's GDE System: A Paradigm ...
-
 从 GDP 到 GDE——如何切断“规模—外汇—互害”的... 2026/02/02
从 GDP 到 GDE——如何切断“规模—外汇—互害”的... 2026/02/02从 GDP 到 GDEFrom GDP to GDE——如何切断“规模—外汇—互害”的制度循环?How to Cut the Institutional Loop of “S...
共生思想理论前沿
THE THEORY
-

-

-

-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Symbiosism:Charles Thomas Taylor &Qian hong又一次量子缠绕...
查看详细说明
Speech
-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 ——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钱 宏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语从金音玉(Yǜ):金口玉言,一诺千金,性人诚恳、执信; &n...
-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点击播放 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访钱宏主持人:...
“权为民所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怎么改?
发布时间:2020/07/06 公司新闻 浏览次数:2717
“权为民所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怎么改?
钱 宏(无党派人士,中国作协会员)
题 记:十三大(1987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十四大(1992):“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十五大(1997):“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十六大(2002):“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2007):“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这里,也谈点体会: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怎么搞?
如果说从1982年小平提出到2002年11月,20年间使用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去掉“有”字,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的发展和认识深化的结果,那么,从16届五中全会提的“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到17届五中全会提“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去掉一个“地”字,是否表明把表达“试探性”的、可能理解为“将来进行时”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从实践发展的需要和认识深化的结果,直接改变为具有“坚定性”的、“现在进行时”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去掉“地”字,就可以理解为“我党的正确选择和伟大创造,是前无古人的中国独创,是中国社会制度”,即包括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在内的主体性结构调整、转变的开始。
“中国社会制度主体性结构调整与转变,从现在开始”——这是我学习17届五中全会公报的一点小小体会。
2010年10月18日
摘 要:
[邓小平在1980年就告诫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权力问题。那么,是什么权力问题呢?依旧不必纠结于阶级分析、主义之争和东西之辩。归纳起来也很清晰,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政府公权的边界与人民、国民、公民人权、事权、物权的边界问题。
[政府公权的边界,从政治上讲,是个“权力从何而来”的问题,从法律上讲,是个“权责对称原则”问题。
[如果说,温家宝指出“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应该要和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不一样才对……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与毛泽东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权力从何而来”的问题相比,更加明确了“权力从何而来”的宪法、法律基础;那么,习近平9月1日在中央党校提出的“权为民所赋”观念,则已经为中国接下来在宪法、法律基础上(框架内、前提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政治上的思想理论准备。顺便说一句,从党纪运作的规矩上看,我相信无论是温家宝,还是习近平,其言论都应当得到过胡锦涛授权。
[权责对称原则,是对以往一切特权的根本否定,也是现代“宪法政治”与“共和制度”的鲜明特征。那么,在宪政共和条件下,政府事权与国民事权的边界在哪里呢?很清晰:对政府事权而言,其法权含义是,法许之内的事才能做(我们制定《行政许可法》就是这个意思);对国民事权而言,其法权含义是,法禁之外的事都可以做。
[国民事权只能受限于自身能量(如思想力、智能、知识、愿景、应变力),除此,国民事权适用于一切法禁之外的领域。这是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进入工商文明形态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获得长足进步的根本而普遍的动力所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民事权大如天!]
从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动组织改革力量的层面看,得幸闻辛子陵先生为代表的“救党派”提出“在民主社会主义旗帜下,在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内,实现党的民主转型,建设执政党和反对党能够互相转化、互相替补的多党制,避免苏联式的土崩瓦解,实现美国式的长治久安,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我对此持积极评价的态度,同时,对“走美国人的道路”还想作点具体分析,感觉还是提“走当代中国人的道路”比较切合实际。因为:
公权力的边界-权力从何而来-权责对称原则-国民事权大如天背后的政治哲学,是当代人交互主体共生新政语境下“主权在民”——“权为民所赋”!

中国政体改革要正确区分“两个一边倒”
我理解,这里说的“走美国人的道路”,与早年共产党人说的“走俄国人的道路”,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本质区别。
相同之处是,第一,作为现代政党政治后发国家的人,特别相信“榜样的力量”,真心诚意地认为,只要做好学生,就能万事大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不要说当年的陈独秀、李大钊,就是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派戴季陶也是这样想的(所以,由他最早动议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一点也不奇怪),而且,当后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搁置“榜样逻辑”,而凭借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高超谋略(战略、战术)真的夺取政权以后,这种“榜样逻辑”的思维方式,重新以“集体理想”(主义)的姿态,占据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整个心智。
第二,用“榜样逻辑”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六十年,从向苏联一边倒,经过中苏关系破裂、“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共产主义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双重失败,逐步过渡到向美国一边倒的“两个一边倒”的治国路线(对不起,我把后来事实上倾向美国一边倒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专家学者社会精英,依然看作是怀有“集体理想”与遵守“榜样逻辑”思维方式的余绪)。
本质区别是,第一,出发点不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出发点是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后继怀有集体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摆脱经济停滞特别是财政危机及民不聊生(下面统称“前者”);而辛老为代表的“救党派”(下面统称“后者”)的出发点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解决经济腿长而政治腿短“瘸腿改革”,避免暴发社会革命。
第二,表现方式和目的不同。前者在过去三十年里事实上也是“走美国人的道路”,但“只做不说”,给自己(首先是当权者)留有选择余地,也为自己作为“利益集团”(与“集体理想”对)以权谋私开了方便之门,结果造成所谓“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和剥削”的格局;而后者实际上要求的是,既然中国已经在“走美国人的道路”,就干脆名正言顺地走,且要全面地走,不是经济上走,政治上更要走,以便让将近8000万党员事实上存在诸多政治派别的全体中国共产党人都有机会走,看谁走得象,走得更好,更有利于全体中国人,继而全体中国人也都有机会走(他们事实上被剥夺了“走美国人的道路”权利),从而走出美国式中国的长治久安来。
从上述同与不同,我们不难发现,都与其社会历史发生学的背景相关联(参看拙作《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1995)。一般来说,社会的构成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意识形态改变加革命改造,如果意识形态一旦与权力结合,陷入原教旨主义,这个社会也就同时陷入各种僵局不能与时俱进,最后社会重新“洗牌”,我们作为榜样的“俄国人的道路”属于这一种。社会构成的另一种方式,是经由历史自然演化加渐进改良,这是独立战争之后“美国人的道路”。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第一任总统时,美国开始也是象前苏联一样实行一党制,华盛顿属于联邦党,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任期结束后,美国的联邦党发生分裂,分裂后的联邦党经托马斯·杰斐逊整合后改为民主共和党,民主共和党在1829年后又分裂为民主党和辉格党,后来辉格党又逐渐演变成现在的共和党。1861年阿伯拉罕·林肯当选,代表共和党首次执政。南北战争后,共和党实行大赦政策,赦免曾与国家为敌的前南方同盟政府人员以及支持奴隶制的民主党人,深受国民喜爱,连续执政20年历经5任总统。然而由于长期执政,许多共和党官员贪赃枉法,腐败无能,引起国民痛恨。这时,在野的民主党也逐渐改变了原先的狭隘立场,转而代表工商企业家、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利益,其总统候选人克利夫兰在1884年大选中胜出,当选第22任美国总统。接下来,共和党人本杰明·哈里森再次当选执政,此时美国工业化臻于完成,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看似平庸的哈里森顺应潮流,签发了国会制定的旨在稳定局势、防止社会动荡的划时代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下文还要讲到)。从此,共和党与民主党通过竞选轮替执政的局面在美国形成,且几乎每一届总统都为美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做了至少一件实质性事情,终于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引领群伦的文明力量。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这就是:既然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走美国人的道路”——我理解的是走“经由历史自然演化加渐进改良”的道路,亦即我所谓的“当代中国人的道路”,那么,再纠结于“阶级分析”、“新老资本主义”、“新老社会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问题,意思不大。而且,有可能再次陷入象2006-2007那场没完没了的无谓的“主义之争”,无功而返毫无结果,还将留下新的社会积怨。
从思维方式上超越“阶级分析”、“主义之争”、“东西之辩”
爱因斯坦说过,“你不能用跟造成问题的思维相同的思维,去解决问题。”必须在思维方式上超越“阶级分析”、“主义之争”与“东西之辩”。
首先,尽管在中性意义上使用“阶级分析”方法,比较方便,但在当下中国,应当考虑到这种划分在人们观念上曾经造成的思维定势,避免以此区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且“敌人是不会自动投降”,从而引导人们走向社会政治革命之路。老实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下,不管哪种形式的社会革命,即使成功了,其结果都很难超越“将坐轿子的与抬轿子的易位”那种“剥夺剥夺者”的历史治乱循环(参看拙作《“共生儒学”论》,2010.9)。那样的话,继续使用阶级分析,只会激发所谓“官僚资产阶级”(有很多界定),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千方百计的反对,包括利用旧有意识形态和手中掌握的媒体搅浑人们的视线,徒劳增加改革的阻力。
2003年我在一篇回答一位曾分管《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负责人询问对“三个代表”意见的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是一个“集体理想与利益集团矛盾运动”的历史,因而必须肯定党内坚持“集体理想”的那部分人士的积极作用。如今,从现实情况和历史进步的双重意义上看,第一,这部分力量在党内是存在的,在位的不在位的、台上的台下的都有,也是中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或改良的中坚,更是所谓“救党派”得以存在的现实依据与合理性所在;第二,这部分力量如果能主动积极推进改革,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方式(参看拙作《从“三个代表”到“社会元勋立宪制”——把握“集体理想与利益集团”矛盾平衡之四种合理可能》,2003.9)。所以,中国社会、人民、国民、公民应当坚决全力支持,不仅如此,一切反对“左倾幼稚病”与“右倾狂躁症”的成熟的富有共生智慧的人们,还要诚心欢迎坚决鼓励坚持“利益集团”的那部分人中分化、转化出来而诚心诚意支持改革的人士,对他们不要求全要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参看拙作《论国家主义与国家权威》,2007。《中国政体改革的动力源与切入点》,2010.9)。
其次,说到主义之争有无必要,还是回顾一下历史。中央党校的蔡霞教授说她悟出一个道理:当人类从农业文明社会转向工业文明社会的时候,先走的是欧美国家,他们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走过去的,走得太痛苦,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所以才有了社会主义这一理念的提出。说到底,在走向工业文明的时候,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社会绝大多数人来讲,怎么样让人们走得不那么痛苦,不那么残酷、不那么血腥、不那么野蛮?从这个角度讲,人类在走向工业文明过程当中,寻找到的怎么解决社会矛盾、怎么减少社会痛苦,所形成的一系列的文化观念、价值理念、制度建设、制度创新,以及所有的这些做法,我们把它看成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而且现在人家还在不断的往前发展。这是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无所谓主义不主义。
我想,这里还是不能不提到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1867年该书出版后仅仅23年,美国通过国会——“代表全民利益”——立法这一更加积极有效而主动稳健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引起社会动荡的“两极分化”的可能性,正式颁布了《谢尔曼反垄断法》(1890)。促使“反垄断法”出台,是马克思对世界的最大反面贡献和文化正果,也是西方社会有能力自身调节生理机制的表现(参看拙作《在信息的激流中思考》,1983)。另外,美国人比较务实,往往是直接把欧洲人提出的主义问题化解掉,而非和其文化宗主欧洲人去比拼主义谁更先进。《反垄断法》生效后,经过福特汽车问世的1910年代和第一次金融风暴,至1930年代国会再度制定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美国就有了与英国1945年的“民主社会主义”相对应“人民资本主义”或“社会资本主义”。
这样一来,美国不但奠定了二战以后的长治久安和世界领先地位,而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消化并彻底消解了马克思的“新贡献”。我指的是,他在给朋友约瑟夫·魏德迈(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信中表达的,他“只是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至此,工商文明形态条件产生的资本主义运动(始于工业革命英国)与社会主义运动(始于1831的法国,共产主义不但早于社会主义,而且早于资本主义。但在马恩那里两者基本是一个意思),就开始合流,进入趋同化发展阶段(参看拙作《迎接世界社会共生主义时代》,2007。《全生态社会建设论——关于我的“共生主义理念”由来的说明》,2006)。
正因为如此,早在前苏联赫鲁晓夫改革的1950时代,苏联共产党就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全新概念。赫鲁晓夫显然是“救党派”,但在中苏嘴皮战中作了牺牲,苏联共产党在经历了冷战危机(对外树敌是统治者保全自己的最后办法)及“爱国主义的最后避难所”之后,失去了主动改变自己顺应工商文明新阶段的进步潮流,最后走向了坟墓(所幸的是,没有经过流血斗争)。
其实,对于“社会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出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预见。他说:“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即社会资本,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股份公司,“应当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即社会资本的——宏注)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最终可能“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875年,马克思在亲自修订过的法文版《资本论》中还补充说,历史上存在过的劳动者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了;共产主义所要重新建立的,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1974年版)。
因此,无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最后都将会走向“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用我这个今人的话说,叫“公民共生体”(参看拙作《公民共生体——整合超越农耕文明和工商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唯一载体》,2008。《共生主义——中国形象的哲学基础》2010)。
至于政治上的“东西之辩”,就更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谁能说这些概念不是西方来的?又有谁能说实际运作过程中没有东方特色?
把思想统一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前提下
基于上述历史分析,在我的理解中,把资本置于优先位置者,就叫资本主义,把社会置于优先位置者,叫社会主义;所以,资本主义并不是“市场自由”和“私有制”的别称,社会主义更不是“政府管制”和“公有制”的代名词。
过去一百年的世界历史也告诉我们,市场会失灵(如生产过剩、资本创新导致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政府也会失灵(如财政过度聚敛导致与民争利的国家公平危机),还会出现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以至于道德失灵(如市场与政府行为机会主义导致社会诚信危机)之“三重失灵”。中国年23万起的群体事件(每一分半钟一起)、1600万精神病重症患者、青壮年男子精子总量锐减80%、财政收入25.7%增长率与国民收到3-5.7%增长之差(背后是低工资高物价,社会福利压力、就业压力与通货膨胀)这些实情也充分说明“三重失灵”的客观存在。所以,任何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不受任何法规限制、不顾社会舆情和不受媒体监督的“专政实践”,对一个民族、国家、社会来说,都是不可取的。
各种迹象表明,人类处在又一次历史大变局之前夜。
在上文中,我已然说明“公民共生体”,将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当代形式。这是基于人类在工商文明的道路上遭遇到地球承受力及化石能源带来的增长的极限、核子生化武器带来的对抗的极限、高速交通和互联网让世界变小、变平以及IT技术超限战对弱势者能量释放带来的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之后,不能不走上生态文明之路来考虑的。历史的进步往往是遵循一种所谓的“倒逼法则”(参看钱宏执笔的《让城市拥有人类的面孔——联合国经社组织国际信息发展网馆荣誉日宣言》,2010.9.8)。
那么,这种公民共生体,不但在实然意义上可望成为世界与中国的建设目标,而且,其中蕴涵的主体间(Intersujective)共生法则、共生关系、共生智慧,在应然意义上也将成为世界与中国的价值目标(这里说的法则、关系、智慧,简单点说,就是通过互助life and let life即“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亦大家都乐乐,不要独乐乐的法则、关系、智慧。参看拙作《共生的智慧》,2008;《共生场——行将来临的革命》,2009)。
至于公民共生体,亦即“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叫什么主义,以什么方式达到,是以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方式(已经证明最终行不通),还是走议会民主斗争的方式(取得不小成果),还是干脆以议会立法的方式(最简捷、最有效、也最稳健)达到这样的目标,完全可以视各地、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与现实状况来定,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名副其实诚心诚意地实行,不要做荀子所拒斥的那种“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来忽悠自己的国民。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公民共生体承载的生态文明形态,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经过每一个个人的自觉和身体力行,就能成为我们的生活实现。请相信这样一条“共生公式:乐活细小行为×我(每一个人)=改变世界的力量”(参看拙作《拯救地球, 亟待克服我们被宠坏的惰性和奢侈攀比的蒙昧》,2009。庆祝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十周年暨首届世界城市发展论坛演讲稿:《后哥本哈根时代:改变思维方式——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组织构想》,2010.9.11)。
基于此,我个人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17大率先全球以一个大国执政党的身份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划时代的历史性事件。
从人类文明成果和文明形态更替的大局上看,讲不讲主义(赞成或反对),都立马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去顺应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流、大趋势,推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去纠结于“阶级分析”和那么多“主义之争”,而是“用人类文明的大视角看待问题”,把中国各路各派人士的思想统一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前提下,以打开更多中国国民的思想空间——生態文明统领,共生思想为魂。
这样,我们的思路就会变得清晰起来,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17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前提下,坚定不移地“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之路”;坚定不移地用生态文明的交互主体共生法则、共生关系、共生智慧来为一切中外古今现存的所谓“硬道理”导航(参看拙作《请用“共生世界”为“无核世界”导航》,2010.4。《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出路:改变思维方式,把气候政治纳入生态政治的框架》,2009.12)。
中国政体改革的关键是政府事权与国民事权的边界问题
邓小平在1980年就告诫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权力问题,这应当没有异议。那么,是什么权力问题呢?依旧不必纠结于阶级分析、主义之争和东西之辩。归纳起来也很清晰,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政府公权的边界与人民、国民、公民人权、事权、物权的边界问题。
因为在我看来,西方人讲的自由,包括罗斯福讲的后来又写进《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四大自由,放在中国语境中理解,就是把自由化约为人的基本权利(同样,西方人说以自由为基础的正义,在中国语境中当为“天下相安之道”,所以也应当化约为人的基本权利)。所以,自由以及正义,说的就是人民、公民、国民的基本人权、事权、物权这“三权”。一切自由以及正义的声音,都必须落实到“三权”运作的社会现实建构之中(参看拙作《公民个人权利优先引论——作为整体主义的共和国公民学与作为个体主义的共和国组织学》,1986)。
“三权”中最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中国所有公民的行事权、做事权。所以,再简化一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个事权问题,即政府事权与国民事权的边界问题。
明乎此,接下来,只要弄清了所谓“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对于即将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中国大陆来说,首先讲的不是经济、技术问题,而是政治、法律问题。讲得再透彻一点,也就是从政治上讲,是个“权力从何而来”?从法律上讲,是个“权责对称原则”问题。
权力从何而来,或权力从何而得、而授、而赋?毛泽东早就提出并指出过问题的要害,是“权力民授”(他提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同时指出:“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了,人民就可以组织起来,将他们打倒”)。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现代政治(工商)文明对“君权神授”、“打天下坐江山”的否定。
如果说,温家宝指出“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应该要和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不一样才对……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与毛泽东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权力从何而来”的问题相比,更加明确了“权力从何而来”的宪法、法律基础;那么,习近平9月1日在中央党校提出的“权为民所赋”观念,则已经为中国接下来在宪法、法律基础上(框架内、前提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政治上的思想理论准备。顺便说一句,从党纪运作的规矩上看,我相信无论是温家宝,还是习近平,其言论都应当得到过胡锦涛授权。
权责对称原则,是对以往一切特权的根本否定,也是现代“宪法政治”与“共和制度”的鲜明特征。那么,在宪政共和条件下,政府事权与国民事权的边界在哪里呢?很清晰:对政府事权而言,其法权含义是,法许之内的事才能做(我们制定《行政许可法》就是这个意思);对国民事权而言,其法权含义是,法禁之外的事都可以做。
国民事权只能受限于自身能量(如思想力、智能、知识、愿景、应变力),除此,国民事权适用于一切法禁之外的领域。这是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进入工商文明形态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获得长足进步(我不大用长治久安)的根本而普遍的动力所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民事权大如天!
落实“国民事权”可以从立法上要分三步走
当前,我劝主张政治体制的人士,也不必过于纠结于宪法、法律条文。因为即使是“82宪法”,及此后的多次修订本,包括写进人权条款这一版宪法(2004),其总体上是一个内部充满矛盾,前后牴牾的文本。
中国的宪法及其几乎每一部下位法,都给有权解释她的机构和个人留下太多的运作空间,简直可以说是怎么对自己有利就可以怎么做。这是所谓“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成为普遍现象的根源。随便问一个有律师执照的人,他都可以告诉你包括宪法在内几乎任何一部法律的内部矛盾,以及有权解释法律者所拥有的方便之处。
这是因为,中国法律制定,首先在立法程序上就存在先天缺陷。
比如1983年到2003年国务院两次制定《出版管理条例》的制定者,可以公然这样解释说:制定《出版管理条例》,而不是由全国人大立《出版法》,目的就是让宪法35条中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也就是说,制订法规的人明明知道自己“违宪”了,却还如此理直气壮。他们知道,立法本来是全国人大的职权,但不能让全国人大直接违背宪法。所以,凡是遇到这种情况时,就由赋予国务院(包括各部委)制定各种有关“管理条例”(以前是“红头文件”)的权力,所以,由国务院授权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制定《出版管理条例》,可以避免了人大自己违反宪法的情况,又可以保证中国的新闻出版行政执法部门“有法可依”。因为中国规定:中央文件、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包括各部委)所制定的法规、条例、规定等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而更重要的是,有权制定政策、法规、条例、规定的部委,都有自身的特殊行业利益,对此,它怎么可能不考虑,甚至不优先考虑自己的行业利益呢?上世纪80年代中国媒体还提“反对行业不正之风”,有关部门也出台过政策。可是,到90年代后,中国来搞起“GDP增长率为纲”来了,于是,经济学家们给了一个说法,叫依靠政府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从此,再也听不到反对行业不正之风这个说法了,因为每个单位、部门都要为GDP做贡献么!所以,千万不要小觑中国官员和专家们的智商与腾挪之功!
再者说,宪法只是一部母法或叫上位法,宪法中的原则规定,并不能直接在民事、政事中加以运用,必须要制定一系列相关的下位法,才能执行。所以,如果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士(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只是呼吁“兑现宪法第35条”中的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有关当局是有太多的办法对大家虚与委蛇。真要讲“兑现宪法第35条”这一国民事权的头等大事,必须抓住立法程序这个源头,这就是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真正的《出版法》。
基于此,这些年来呼吁“兑现宪法第35条”的人士,应当紧紧抓住“制定《出版法》,废除《出版管理条例》”这个关键环节!
有关当局不是不明白大家说的道理,“违宪”是事出有因(对不起,他们的智商绝对不比别人低而很可能相反),所以,必须首先抓住关键环节,比如就“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关键环节,第一步是废除现行《出版管理条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法》。
第二步,就是要废除国务院(政府、行政机构)各部委制定法规、条例的权力。在这里,改革,不是“放权”而恰恰是要“收权”,即: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把所有立法、立规的权力收到自己手里,在立法程序上,坚决改变现行“部门立法”的立法程序。
最后,当然是要修宪(如果修订结果比较理想,应当全民公决通过!)。但是,在没有办法做到全面修宪的情况下,可以先制定一部《国民事权法》(实际上,这是一部与人民共和国相称的“小宪法”)。制定一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没有的《事权法》,这才是中国人和中国特色的独创(参看钱宏《百年民生路,亟订<事权法>》、《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为什么经制定<事权法>?》,2010.3)。
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诉求,首先应当在国家治理层面上集中力量,从法权上界定政府与国民的“事权边界”。
然后以此为圭臬,来重新修订我们共和国的宪法,否则,说一千道一万,包括宪法政治、宪法整体在内的公民的单项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自由”,永远会流于条文而落不到实处。
这同样是“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之路”的具体展开。
支持中国领导人从自己“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
中国目前的无序混乱状态必须改变。一切希望中国进步和希望中国走上正轨、常规、常识的人们,自己要有清晰的思路,一定要避免任何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无序行为(在明白自己的价值诉求的情况下,还要讲求起码的逻辑思维)。
在一个激情极度匮乏的年代,我想特别提醒愿意燃烧热情的人们,珍惜自己,把力量用在该用的地方。比如,温家宝总理已经清晰地表达:“尽管社会议论纷纷,尽管遇到阻力,我仍会坚定不移推动我的信念。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那么,那些钻温家宝总理空子,对他苛求的人们(荀子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器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当敬其宝、受其器、任其用,除其妖。”退一万步说,温总理还是“国器”。所以,无论是从左还是右的方向反对、嘲笑温家宝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士,不是什么勇士,而恰恰是怯懦和无能的表现),特别是那些寄希望于温家宝的有识之士,以其帮着他反驳反对政体改革的言论,不妨给温总理写封公开信建议:
请温家宝以国务院首脑的身份与权限,主动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提出变革中国的立法程序,国务院以及各部委行政执法机关,不应当承担立法包括制定法律意义上的条例、规定的职能和职责。
向全国人大提出“国家行政执法机关,不承担制定法律意义上的条例、规定的职能和职责”,正是温总理“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的重要一环。这样,我相信温总理今年3月“两会”期间表达的全面改革,和他呼吁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开始上路了,启动了,落到实处了!
至于大家关心的为某个历史事件“平反”,那显然不是温家宝总理能力范围内的事。而且也不是一件单纯的事。2006年,我在作《邻居的伟大与幸运》时特别提到:1996年7月4日的第二轮投票中刚刚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叶利钦获胜,再次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同年,叶利钦即签署总统命令,将11月7日这一天命名为“民族和解与团结日”,此举与中外历代开明君王登基时,即宣布“大赦天下”对社会稳定与文化创造的作用——如李白、杜甫都曾受惠于此——有异曲同工之效!中国一百年、六十年、三十年来的社会积怨太过深重,历史包袱太过沉重,单靠某一股走上前台的政治力量,以跟自己有无干系或是否受害者划线,去“平反”、“大赦”某一次事件(如彭德怀事件、刘少奇事件、“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失败、失势、失落者,已不足以解决当下中国动员全体国民进入社会政治经济全面改革的历史需要。
中国的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导致社会积怨的历史事件,除了真正涉及“国家机密”的事,必须一次性不留尾巴地加以解决,中国人民和政府才能轻装上路。
我祝願當下中國,每一個有權、有勢、有錢、有知,一句話,有影響力的有組織的和非組織的國民,都懂得一點“共生法則”、“共生關係”、“共生智慧”、“共生價值觀”——交互主体共生新政(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Policy (ISP)):遵循全民共生价值观,搁置阶级分析和主义划线的意识形态纠结,超越左、中、右、主流、非主流的政治划界争端,全民全官互为主体,以便“对内实现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國形象”,轻装上阵,去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
这需要全国人大授权国家主席以大智、大勇、大慈悲之心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对内实现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国形象”的国策。
这是当代中国摆脱农耕文明时代的“帮派政治传统”(总是一部分得势者去“和谐”另一部分失势者,导致有人欢喜有人愁),使全体国民由衷产生“国家认同感”(当前,中国国民有无“国家认同感”的试金石,是人们是否主动把存到外国去钱取回来,把送到国外的子女请回来搞建设),从而使“人民共和国”名副其实(参看拙作《公民个人权利优先引论——作为整体主义的共和国公民学与作为个体主义的共和国组织学》,1986),成为现代正常国家的必由之径!而这,依然是“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之路”,“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的题中应有之议。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复述一下《邻居的伟大与幸运》(2006)一文中表达过的观点:“历史的前进,不能没有历史人物的推动。历史人物并非不犯错误的人,恰恰相反,他们可能比谁都会犯更多的错。同时,历史人物之所以为历史人物,也不在于他自己做得多么出色(甚至有可能相反,一时间可能使他及他的国家陷入一时的困境),而在于,他能够将他比任何人都更强烈而明晰的历史感,诉诸现实行动并引领人们前进。他们适逢其时,顺应其势,站在新旧交替的风口浪尖,不断从瞬息万变的对局中抓住生机——你可以说是他个人的生机,但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生机——而真正的机会往往只有一次,可谓稍纵即逝,谁能更为准确无误地把握历史的脉搏和律动,谁就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人物!”(另请参看拙作《中国亟需一代社会元勋,时代呼唤千载历史人物!——中国政体改良中道路线图》2003-2010)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Policy(ISP):当下中国,正值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转机期!
让我们相信,能抓住这次历史生机的历史人物,就在当下中国的高端领导人之中。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尤其是以不同阶层利益代言人自居的左、中、右派人士及媒体界人士,自己应当成熟起来引导人们树立这样的观念:谁能推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及其社会政治进步,即帮助中国“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大家都应当欢迎!
请相信,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国民,已作好了接受“交互主体共生新政”(ISP)的准备!
2010年10月7日于天通开关居
此文全文刊载《明镜》月刊2010年11月号封面第二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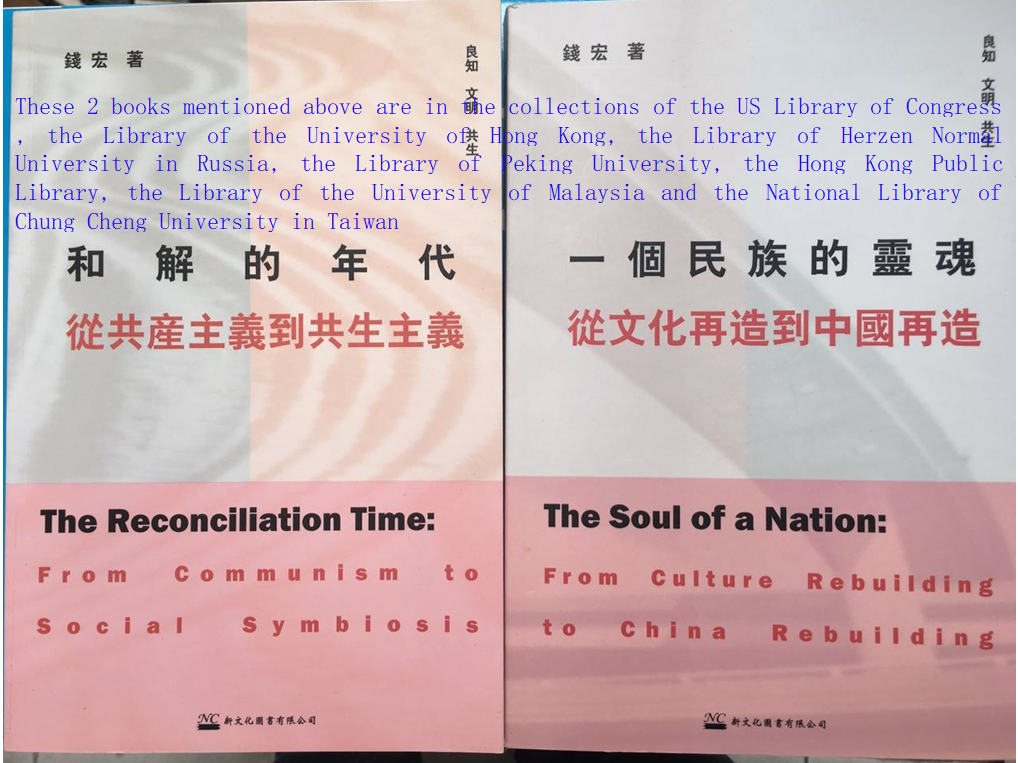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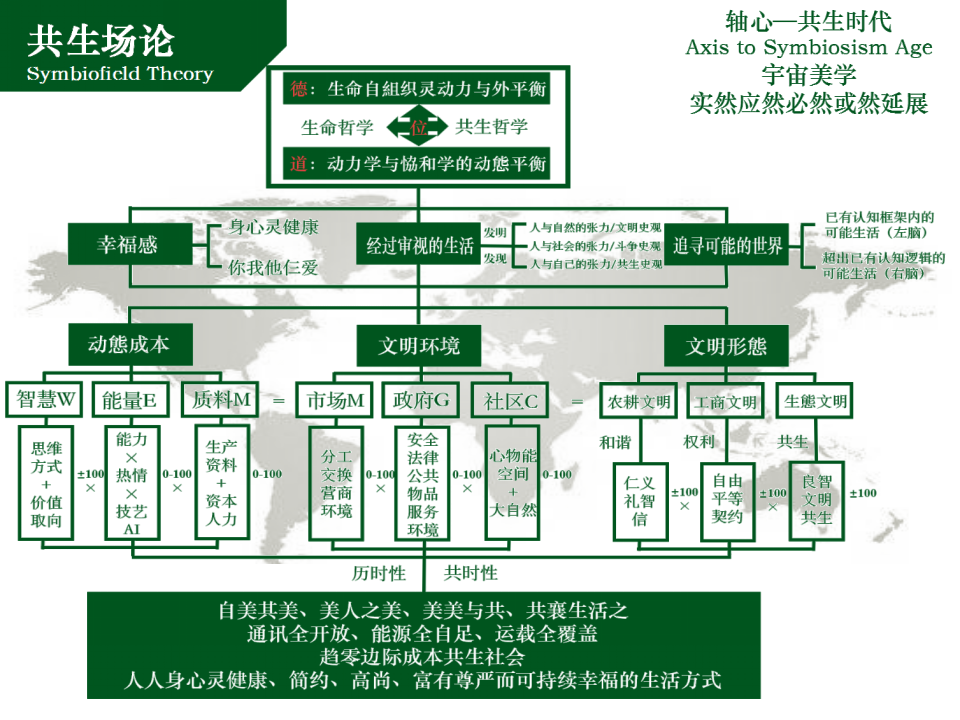





作者的历史认识和未来设想是好的,但在中国当下的文化状态下,请有大气魄当权者主动的大幅度的政治改革,即使出现了,也会造成类似休克疗法的后果,因为文化传统影响和现代民主自由的群众思想本能基础跟不上,而且美国也面临政治体系必须大改的问题,等待互联网全球多元时代文化教育浸泡吧,少年强则国强!
2022年05月26日上午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