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Articles
-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2026/02/24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2026/02/24【共生经济学·前言】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The Cognitive Bias and Fragmentation of Economics as...
-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2026/02/22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2026/02/22《共生经济学》自序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How Should We Face the “Ultimate Free Lunch”? 一、从宇...
-
 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2026/02/17
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2026/02/17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Modern National Normalization under the Global Symbiotic Paradigm ...
-
 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2026/02/16
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2026/02/16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Chinese Reproductive Officialdom: Why Regime Change Has Not...
共生思想理论前沿
THE THEORY
-

-

-

-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Symbiosism:Charles Thomas Taylor &Qian hong又一次量子缠绕...
查看详细说明
Speech
-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 ——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钱 宏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语从金音玉(Yǜ):金口玉言,一诺千金,性人诚恳、执信; &n...
-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点击播放 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访钱宏主持人:...
中国政体改革的动力源与切入点
中国政体改革的动力源与切入点
柳江您好!
很高兴与您结缘。一口气读完了你给我的七篇文章,非常佩服你的洞察力,且很欣赏你的文风,这都是我要好好向你学习的。
中国政体改革动力依旧源自权力核心
我同意江的综合素质高于胡的判断,这也许主要是他们早期教育背景不同使然(江年轻时的中国教育比较正常),还有,相对来说,江敢干一些,且没有那么深的城府;而胡相对保守且城府很深。
不过,我想说保守并不是与进步相对,而是与激进相对,所以,保守未必就不会进步。完成英国光荣革命的政治力量,其主要推手就是保守党的前身托利党人。
此盖因江未经过媳妇熬成婆的的磨砺,是突然直升上来,尽管当时还提心吊胆地应对陈、邓双方拉扯,但凭借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侥幸而成功地越过三年考验期而后获得基本自主权——我曾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四种可能》(2003)、《如何解决“7000万人法定金饭碗”的问题》(2006)、《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及政府与公民的对峙》(2006)、《如何看待1978-2006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资本实践》(2007)等文章中都有分析——这里不评论江此后的十年。而胡,则系隔代指定接班人且最终接到了班,熬了整整十年,政权得来相对不易,这注定了他哪方面都得罪不起,都不敢怠慢,心里掣肘负担过重可以理解,据说“手枪”(中央警卫局)至今握在忠于江的人手上(当然,这也许是胡系人的一种辩解或推托)。所以,他总是先试探一下(如第一次政治局学习的内容是宪法课,在怀仁堂开民主党派领袖会议强调增加他们的参政深度),不行马上退缩回去。因而大家看到的胡,似乎总是说一些“宽松”的话,但紧接着出台的措施却更加“收紧”。这样,从2003年众望上台以来,经过一次次希望的落空之后,人们对他不免异常失望,尤其是北京这个地方的人。不过,我本人还是对胡抱有希望,感觉还不能完全排除他也许步齐威王、楚庄王之后“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可能。
但是另一方面,当我看了你写的《江泽民瀛台问学沈志华——江泽民60大庆之夜致信中央背景揭密》后,我开始同意你说的江、胡政体改革竞赛中,江可能反而会走在前面的意见。江能在60大庆被高抬的当晚,不是心满意足(被捧晕)而是有感而发自觉进入60年的反思,足见江还真不是一般的人。而且,只要江愿意,他现在确实也有条件从容不迫地考虑一些当代中国发展的真问题,甚至去碰一些硬问题,把许多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正本清源。
然而,江要转过这么大的弯子来,恐怕也还没有那么容易,主要是他还没有自己创新性的可替代性的思想理论。其次,毕竟江已经不在一线,中国年23万起的群体事件(意味着平均每一分半钟一起)、1600万精神病重症患者、青壮年男子精子总量锐减80%、财政收入25.7%增长率与国民收入3-5.7%增长之差(有人将中国的低工资高物价与美国的高工资低物价相联系,似乎更能解释这个“剪刀差”越来越大的原因,反过来势必导致创业压力下降、就业压力增加与通货膨胀)等等,对于他来说,并不够成“非转弯子”不可的紧迫感!如果江有“紧迫感”,有些事他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比如,他让陈奎元先生邀请戈尔巴乔夫不成,还可以自己要求秘密访问俄罗斯,秘密拜访戈尔巴乔夫及他的一些“老朋友”不是吗?再比如,他既然问政于沈志华,那么,江也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建议有关方面把前南斯拉夫副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创始人之一吉拉斯(Milovan Djilas)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与普京2006年任总统时委托俄罗斯历史学家祖波夫(1952-)主编的《20世纪俄国史(1894-2007)》翻译过来,直接发到县团级领导干部阅读。该书由40余名专家合作写成,读者对象是相当于中国的高二、高三学生,其编写动机很简单,就是这批历史学家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
相反,胡在一线,应当是有紧迫感的。所以,包括温在深圳三十周年纪念前夕关于政体改革的讲话,我宁可相信背后有胡的认可至少默许,对胡来说,方法依然是作试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感觉传闻中有关胡打算搞“社会主义两党制”的匿名信,还是有几分真实性。该信说“18大以后中国的政治巨变的可能性之一,是可能就是让/把共产党分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名称还没有确定),而胡锦涛以非党员身份继续领导军队保证政治转型的稳定性。……温家宝最近的言论,据说也是为了18大以后这样的政治展开做准备。胡锦涛这样计划,据说是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工程’超出原想象,特别是自从苏联的一系列档案的公开和被翻译成中文,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已经破产,使胡锦涛下定决心搞‘社会主义两党制’(与美国的‘资本主义两党制’对垒),正好也使他可以名正言顺再干五年或更长,开启真正的胡锦涛时代。”
但是,胡与江一样,也没有自己独创性的可替代旧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由于没有新思想理论来建构新的政体,同时,由于中共是一个意识形态党——自从搞合作化、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后,中共就丢了基于“耕者有其田”与“统一战线”(向国民党一党专政争民主、自由)“打天下坐江山”的传统合法性,而依靠意识形态的“最最先进”性及其武装力量与管控的媒体力量作为合法性依据——所以,尽管旧的意识形态在江、胡心中及整个中共内部早已没有真正的虔诚和尊重,没有市场,但还得变着法儿,就算是玩弄概念游戏欺骗自己也只好硬挣着。
最新的证据,就是昨晚新闻联播中介绍吴邦国将在10月1日第19期《求是》发表《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文章依旧是用罗列的方法陈述伟大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成绩的原因除了继续讲“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之外,加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积累、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讲到存在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路径时,就乏善可陈,只能回到与取得成就同一个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且试图说服读者中国存在问题的原因是“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意味着可以理解、应当接受),倒是文章结尾,重申了2007年后很久不提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
我相信,以江、胡的聪明才智和对于内外情况的了解,不可能不明白这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游戏,比如仍然坚持把党的意识形态看成是全民意识形态,仍然坚持把党的历代主要负责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意识形态的理解、概括和具体表达形式看作全民、全社会意识形态的唯一价值来源,在逻辑上完全不通,理论上无法自洽,在事实上根本做不到;现比如仍然坚持把党的工作重心,等同于政府的工作重心,进而把政府的工作重心,等同于全社会、全民的工作重心,无法保障其历史连贯性和尊重现实世界的差异性、丰富性。因为,比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阶段,导致这些年中国一切政府性组织、享有行政级别的准政府性组织、一切社会组织的工作重心都是抓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换句话说一切行业都要变成产业、全民都要经商。如此一来,中国将继续陷入无法协调、处理中央现在提出的“转变政府职能”(从全能管理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无法确保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机制体制的改革,不会遇到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激发出来的部门利益、基层政府组织利益发生现实冲突?而发生冲突之后,又如何确保中央决策的贯彻执行,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动力和依靠力量是什么?(钱宏《还原历史和思想理论的真实、鲜活与美感——读<凝聚在伟大旗帜下>,致任仲平同志》,2008)
一句话,坚持旧有的意识形态与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旧有意识形态与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职能以及“调结构”的方针政策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我之所以要和你讲吴邦国今天发表的这篇文章,是因为我当即想到了你说的“江胡政改竞赛”。如果吴代表的是江,那么,正好说明我前面所述,江问政沈志华后,依旧既没有新思想理论作为政改和统领全局的支撑,更没有“转弯子紧迫感”(这也符合吴自己即将淡出中国政治舞台不求进取但求无过的心态);如果吴是胡授意撰文,那么就可能有二可,一是让江系色彩很浓的吴来说这些话,意在澄清江比胡更有改变中国命运的活力的印象,同时顺带表明江、胡并没有什么分岐,二是虚幌一枪,进一步“故意”证明北京人对胡的习惯看法。所以,我依然没有放弃对胡的一点幻想——他的确面对着一个把中国推向现代正常国家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不可能看不到这样的机会么!
中国政体改革应从何处切入?
那么中国的政体改革究竟有没有可能开始,应当从何入手?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过一个“中国新文化论坛”,论坛的主题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出发点,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在什么旗帜下进行。
会上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王占阳、徐景安先生提出“邓小平理论遗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发现”,认为1999年后把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建设”两字拿掉,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既成事实,因而实际上等于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中止。而蔡霞先生则认为,王、徐提出的其实还是在一个意识形态的中国,人们往往习惯了说话做事包括改革,总要戴一个什么“主义”的帽子来进行的问题。其实,要学习邓小平,就应当“超越主义之争,用人类文明的大视角看待问题,也许能为我们解决中国发展进步所面对的问题打开更多的思想空间。”我想,这两种不同观点提出了一共同的问题,就是:中国政体改革从何处切入?比如会上辛子陵先生就直接提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从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开始。”
不过,在我看来,撇开旧有意识形态(即名不副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纠结,而直接以胡主持的17大上率先全球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做文章,完全可以获得全部思想理论上的支撑,不管提什么主义,不管什么性质的党来执政,都需要满足中国突破“社会主义没有社会”框架,突破不同身份资历的公民享受不同“国民待遇”的法权界限,从而满足“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的现实诉求。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人士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也没有太大的风险,所以,是中国公民应当高高举起的旗帜!
工商文明,跟它之前的文明形态有一个基本相同点,就是它在政治上还基本属于地缘政治形态,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种权力关系,所谓权力关系它就是一种支配关系,就是谁战胜谁,谁支配谁?遵循的是“特权法则”,在支配的过程中,谁想占据主导地位,以前马克思时代看到的工业文明也好,我们现在的已经现代化的工商文明也好,还是我们每天生活工作中际遇到的人和事,所面临的矛盾,无非是在这样的支配关系中争夺主导权,想占据超过平均利润率以上的好处和优势。不管是借助政权,还是借助财权,还是借助其他的权力,如身分等级、关系网、知识、信息等等。结果,无论在生产方式上,还是生活方式上,人们追求的是无限扩张,奢侈攀比,这是工商文明的人际关系、群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实质。这次美国金融海啸反映的突出问题,就是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实现欲望的理性工具的有限性之间的永恒矛盾,所以,它没有超越以前农业文明的这样一种关系。
中国是一个宗法亲情社会,讲的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政治上讲的是“内外有别”、“己和异己”,在意识形态上必然党同伐异,在组织形式上必是帮派政治,如果自身强大,必是扬眉吐气傲视群雄,如果自身羸弱,必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而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的基础搞工商文明建设,势必遭遇较之所谓发展国家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在缺乏公共意识的“私人”社会文化条件下,如何行使“国家公权”的问题。
那么,生态文明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呢?它是一种生态政治,它应该建立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遵循的是“共生法则”,简单点说,就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英语表达是:life and let life)。生态文明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国与国之间,不管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一种共生关系。共生法则和共生关系势必要求人们过一种内敛的健康、简约而高尚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如果从生态文明的角度,这样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去考虑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比从什么什么主义角度谈,不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结,还可能会显得更加清晰一些,有利于看清什么是真问题、硬问题,而集中大家的精力、智慧和勇气加以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我很赞成小平他不讲姓社姓资的争论。说得更透彻一点,因为金融危机,各国都在采用政府“救市”的措施,这使得我们对以前一直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政府管制、政府调控,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市场自由,这样的观念固化起来,特别是看到中国目前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相对较小的情况,给不少人(特别是那些迫不及待要强化所谓“中国模式”的先生们)造成一个假象,说什么现在要“靠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
其实,资本主义并不等于是市场自由,社会主义它也不是政府管制的代名词。这里面,我们管什么叫主义,实际上就是把什么东西放在一个优先位置,资本主义是把资本放在优先位置,社会主义是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那么我们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社会主义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建设”,它可能是我们接下来应该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要还原所谓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本意,这里面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17大报告在上海最后一次征求“上海社科界代表座谈会”上(2007.9.7),我提了一条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应当继三十年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现在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整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今天,我依旧是这个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解决“社会建设”的这个前提性问题,就是建设“有社会的社会主义”。
现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争论的焦点,什么制度优势呀,民主自由呀,宪政法治呀,权大法大呀,都可以集中到这个思想基础上来加以评判。政府与公民的事权边界不确定,所有争论都是各说各话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每一种声音的背后,都只是代表着一种利益之争,而不能反映中国国家及其全体国民的基本法权和共生价值。这也是我从来不,或很少谈论“言论自由”、“民主法制”这些概念的原因。
在我看来,西方人讲的自由,包括罗斯福讲的后来又写进《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四大自由,放在中国语境中理解,说的就是人民、公民、国民的基本人权、事权、物权这“三权”。“三权”中最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公民的行事权、做事权。而且,公民事权只能受限于自身能量(如思想力、智能、知识、愿景、应变力),除此,公民事权适用于一切法禁之外的领域。这是一个国家进步的根本而普遍的动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民事权大如天!
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诉求,首先应当在国家治理层面上集中力量,从法权上界定政府与公民的“事权边界”。然后以此为圭臬,来重新修订我们共和国的宪法,否则,包括宪法政治、宪法整体在内的公民的单项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自由”永远流于条文而落不到实处。
我并不是不赞成呼吁中国的民主自由,可是,我从自己的亲身体验考虑再三,所谓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等等,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事权上。如果同为一国之人民、公民、国民,有的人享有超越“国民待遇”和宪法规定的事权(往往是假国家之名、公有制之名,握政府公权之实,行一己之私的无边事权),而另一些人(注定是被称为“群众”的多数人)连做事、行事的基本权利都是问题(比如1956年以后,人民特别是农民连按照自己惯习休养生息“种地”这种行事权都没有,国民连在自己的国家开办公司、厂房、学校、医院这种行事权都没有,公民连按照自己的意愿在选举人民代表选票上划圈圈的行事权都没有),还哪里来的这些自由?当萧默先生的《一叶一菩提》被无端禁印时,他为什么愤怒地喊出:“谁说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我就跟谁急!”他要表达的就是国家(政府部门)的事权大到无法、无天、无边!
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先要从法权上确立每一个中国人的“国民待遇”,特别是“国民事权”。同时,宣布“对内实现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国形象”,以消弥一百多年来无数次的战争、政治运动、资本积累累积下来的仇恨与怨气,逐步培育起全体国民的“精神自立”,从而重新获得社会改革、改良的动力。同时,确立每一个中国人“国民待遇”,应当从确立政府事权边界开始,因而我认为,不必讲那么多公权人士不习惯的民主呀,自由呀,主义呀,只要强调人权、事权、物权对于国民是天经地义的,而在这“三权”中,最重要的是事权——中国百不逾的主题流变。这是中国公民获得“国家认同感”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
我十分赞赏秦晓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制度不是目的,它是一个手段,是一个保障,制度根本上是为了保障实现一套核心价值观”,而“正是由于我们缺乏这样的一套核心价值观,才导致我们社会出现诸多问题”。他的这个发现,也是我提倡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的动因。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基本法则,就是共生法则,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群体关系、国际关系,就是共生关系。共生精神应当成为现时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谁能让社会主义的共生法则成为当下中国政府行为规范与公民行为规范,谁能领导中国通过“对内实现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来建立普及中国与世界的共生关系,谁就是我说的社会元勋!
2010年10月1日于北京郊区
作者:钱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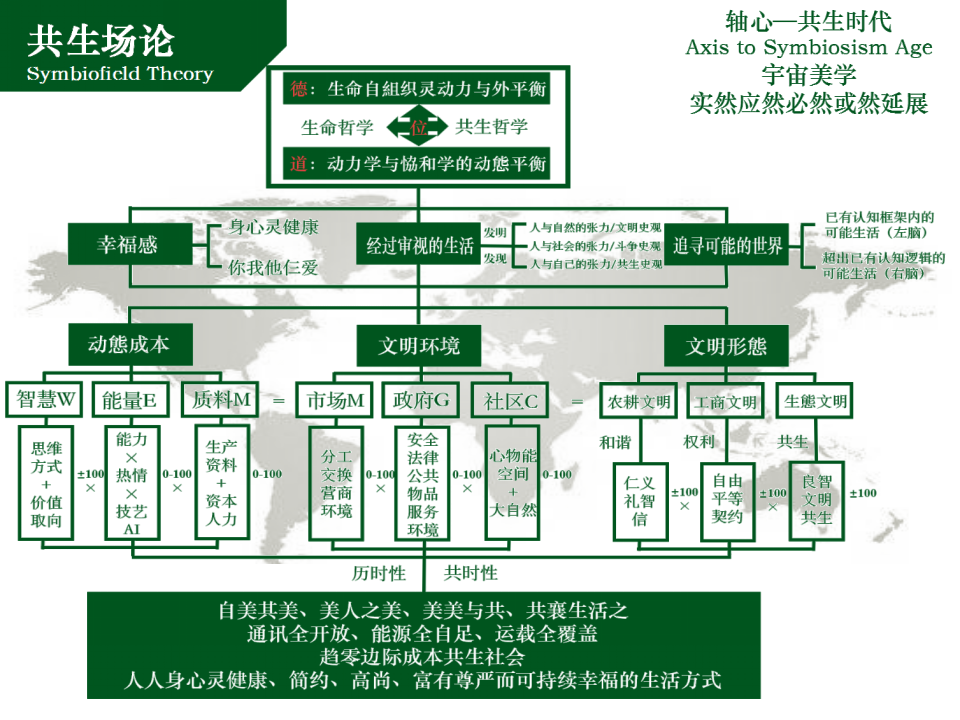





您好!请登录
已有0评论
购物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