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Articles
-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2026/02/24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2026/02/24【共生经济学·前言】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The Cognitive Bias and Fragmentation of Economics as...
-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2026/02/22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2026/02/22《共生经济学》自序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How Should We Face the “Ultimate Free Lunch”? 一、从宇...
-
 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2026/02/17
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2026/02/17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Modern National Normalization under the Global Symbiotic Paradigm ...
-
 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2026/02/16
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2026/02/16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Chinese Reproductive Officialdom: Why Regime Change Has Not...
共生思想理论前沿
THE THEORY
-

-

-

-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Symbiosism:Charles Thomas Taylor &Qian hong又一次量子缠绕...
查看详细说明
Speech
-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 ——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钱 宏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语从金音玉(Yǜ):金口玉言,一诺千金,性人诚恳、执信; &n...
-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点击播放 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访钱宏主持人:...
我的知青生活:想好必干!!!
发布时间:2022/01/01 公司新闻 浏览次数:914
我的知青生活:想好必干!!!
——答《周末文刊》问
寒年路甜玉興
知青之謂意无家
緣去缘来皆安昂
天真幼稚憑傻勁
何可得失非权衡
愛通乾坤思千載
有道无道間道成
乘桴浮海觀世界
孞烎言必稱共生
2022年1月1日于Vancouver
按语:一个半小时后,就是公元2022年了!本想和去年、前年一样,写个新年弘愿,但看了陈春花的新年献词、X老庚的新年致词和方方的祝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在想一个问题:我自己这几十年,是怎么活过来的?自然还有:接下来我又该如何Live and let live?
于是,我打开电脑,竟发现2012年组织发起“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后不久,写过一个答《周末文刊》问,看了一下,自觉还有点意思,上面还引用了甘地的话,就把这个在共生网上发一下,聊作我的新年心音吧!
孞 烎2021年12月31日于Vancouver
《周末文刊》2012年第30期
有请插过队的老知青,报一下你所在队的工分值,或者日工值,和在本公社数上中下哪个档次。并请报出你所在省和所在队属于农林牧哪个区。
用一种温柔的方式,你可以撼动世界。我们人类伟大的地方,不在于改变世界,那是原子时代的神话,应该是能够改变我们自己才对。
——默罕默德·甘地
(改变世界,必定要先摧毁世界,这种野蛮的做法荒唐且虚无,人类是由个体组成,一个个个体最有效的行事方法就是从自身的改变做起——我相信每个生命活体本自具足又非独存,你我他都具有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没有敌人,只有病人,而若有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编辑同志:
我于1969年随父母下乡插队落户(实际上1968年我已经在农村给农民做短工),至1979年回城,务农11年(是失学、医患、体验、观察、思考、实践。期间,1975年在景德镇做了近一年农民工)。这11年其中,知青生活约4年。
1976年父母和弟妹返城,我因早过18岁,按政策不能返城,只能由一般务农人员,转为“知识青年”身份,并转入“江西省都昌县北山知青林场”。我所在的这个林场,当时有60多名知青,基本上是县商业局和教育局系统的知青。收入情况大致是:1976、1977、1978都是,日10个工分满分劳力,合0.12元。
对于这段知青生活,我曾经有点记录(见《我的心路历程——爱通乾坤理,思接千载情》),不妨摘录于下,聊供一哂。对不起,请允许我从记事开始,至返城后的两年,这样也许能看到一个“思行者”是如何从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心路过程,虽然只是一些片断。
1958年夏天,在庐山避暑,看过动画片《东郭先生和狼》、《鲤鱼跳龙门》、《神笔马良》,喜欢和女同学一起洗澡,经常遇见苏联叔叔阿姨笑得好可爱。我的乳名叫“克洛夫”,听起来就有点苏式,实情也是因为父母亲年轻时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对祖国的未来怀有最美好的憧憬,于是分别给自己取名为“克宁”和“洛真”,当他们第一个儿子诞生时,感到这个新生儿就是自己信仰与憧憬的成果,于是给我取名“克洛夫”,意为“真(马列主义)与美(洛神)的结晶”。
1961年冬天,因父母下放刚念半年小学一年级就失学了,县实验小学班主任邹老师追到90华里的大港公社质问家长:“这么好的学生为什么不让读书?”;失学后一边带弟妹,一边跟母亲间或学习。记得小时候的理想,无非是养好多好多的小动物,种很多花草树木。
1964年,复学直接读四年级。1966年学校(小学部)组织跟中学生一起去游行,因自己不觉鬼使神差地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的口号给喊反了一次,而再次失学。1967年父母都响应号召去串连,我带着弟妹在一间空荡荡的小学校舍,经常被周围村子的孩子追打欺负,和他们打混仗玩围城攻城的游戏,还养了五条小花蛇和一只小白猪。
1968-1969年上半年,因父亲遭迫害,全家几次险遭饿死。我帮助母亲挨家给当地农民做短工餬口(吃三顿饭拿三眼米或1毛钱回家)供养弟妹,或偶尔给农民“补套鞋”(雨鞋)赚几毛钱度日。
平生第一次花自己的钱买了第一本书——《毛主席诗词注释》(定价0.77元,这相当于我八个工作日94个小时的劳动薪酬,不知当时为何会舍得)。那时,母亲的乐天性格和老庄式的通达处事为人的态度支撑着全家人,由于不准缝纫(家用缝纫机被查封),不准开荒种地(因是非农业户口),又无钱购买“商品粮”(有粮票),全家人吃的经常是树皮、草根、糠粑和观音土,也决不沿途乞讨,一年冬天我与5岁的小妹路过一口干涸的池塘底部,竟发现一只大团鱼(鳖)藏在泥瓦里,结果从泥沼里一下找到了大小十二只,全家乐不可支认为这是上天的特别眷顾,于是,还把几只小的拿到有水的池塘里放了。
一次,母亲特地告诉我“如果我也被牵连,你要带好弟弟妹妹”还把她从外婆那里学来的一些中草药知识教给我,如可以止血的夏旱莲、治蛇伤的半边莲等说“以后可以用得上,给别人行行方便也好”,我一边学,一边忍不住眼泪直流。那时,无论这家人漂流到何处,遇到怎样冷漠、麻木、鄙视或恐慌的目光(包括亲朋好友),每到傍晚,人们总能听到母亲爽朗而优美的歌声,晚上母亲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如《一朵小红花》、《阿凡提》、《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鲁班的故事》、《今古奇观》等,也给了少年的我最好、最美的心灵滋养——那是一段真正饥寒交迫,但精神自由且意味深长的时光。
1969年下半年,经父亲的朋友帮助落户到南边江家咀村劳动解决全家餬口,我承担起和10分劳力一样劳动强度的劳动,如扛水车、打禾府、耕田等,却因为年纪小只能评最高的妇女工分标准,即7分/天;一次在水库工地劳动中间休息时,工地发放预防瘧疾的糖衣药丸,这是毛主席对贫下中农的关怀,我吃到嘴发现药是甜的,就问药怎么是甜的呢?有人说“你傻子啊里面是苦的”,这回又是鬼使神差,我嘴里竟蹦出一个成语“糖衣炮弹”!于是立马受到批判说这是现行反革命言论,晚上大队部组织开批斗大会,人们高呼“打倒克洛夫”,幸好工地宣传队队长(一位漂亮的上海女知青)站出来说“我看克洛夫年纪还小,不是故意的”,喊了一阵口号后批斗会就结束了。但是回到家里,母亲作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为了我的前途必须逃离这个南边江村(半年前正是它收留了我们!)。在得到邻县大阿姨的邀请信后,一天,全家趁着月色连夜逃走到鄱阳县山里袁家堰村的姨父家,于是,我们又恢复了自由但全家饿肚子的生活。但是在那里,我跟姨父姚毛水学会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姨父经常给我讲他自己的故事,还有《马三借衣》、《桃园结义》这类颂扬人间友谊和立志的故事。
1970年3月,终于获得上方批准全家下放,指定到都昌县苏山公社正式“落户”(再不“落户”真的会饿死!)作“务农少年”。目睹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从一次偶然给农民治好刀伤大出血的经历中,我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体验,加上在鄱阳县流浪时经常上山采药的经历,我开始着迷于中医药学,一边忙里偷闲纯义务采药行医,一边在田头山脚听长辈们(当然主要是“贫下中农”)讲过去的真实故事和他们的现实感受。同年,在生产队会计那里经受一次写不全借条的屈辱体验后,开始在每天12小时的沉重体力劳动之余,偷偷学习文化知识,主要是读鲁迅、高尔基先生的书(后来还有俄国、法国、德国、英国作家的一些书)和毛泽东先生的书(后来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先生的书),当然还有医药书籍(后来还有李约瑟、丹皮尔、爱因斯坦、汤川秀树、海森堡、普里高津先生的书)。由于这三种文化知识分别与人的心灵、社会历史和自然世界相关联,经过这三种文化知识的滋养的我,似乎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文化水平虽不够科班专业深厚,但在结构上,也许比较完备合理,例如我从来不认为自然科学可以与社会人文科学完全分开,反过来也一样。此外,不喜欢同龄人,只喜欢和老农和从上海来的有历史问题的人们往来,他们教会了我许多当时主流媒体中听不到的知识、信息和事实。于是,我开始由一个自卑的叹息少年,变成比较自以为是的沉思青年,甚至由于常年被太阳晒得漆黑漆黑的,有些老气横秋。
1971-1973年,先后有五件事给成长中的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第一件事,是偶然在公社李秘书(父亲的朋友)处读到毛主席给江青的信,不明白为何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有自己的烦恼,他说自己不当国家主席说林彪要设国家主席就是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还有那个山洞很让我好奇(因为毛主席是属蛇的,正好比我大一个花甲60年)。
第二件事,是与生产队长发生激烈争执,队长让人到大队部汇报后抓住一次在水库工地我偶然迟到的错误晚上开起有全大队民工参加的批斗大会,说我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最高指示,“不安心务农”等等,还特地找来五个“四类分子”作陪斗。没想到少不更事的我反而愤怒起来,历数队长的错误行为,坚持认为队长是以地方宗族势力歧视我这个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外来户,说今天开批斗会完全是打击报复,结果,几个邻村的贫下中农当场哄笑起来,有一位农民伯伯干脆站起来为我打抱不平,大家都说队长不对,于是主持批斗会的民兵营长赶快宣布批斗会结束。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到震惊的是:我居然走到坐在台上的队长面前伸出手说“对不起,队长,其实我也有错,请你原谅,以后我不会和你争了”,队长也满脸通红地伸出了手。后来,一次组织打靶我竟得全营唯一优秀后,那位民兵营长和那位打抱不平的伯伯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还让我当了采石队爆破队队长。
第三件事,是批林批孔时读到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解放全国“四类份子”的话,第一次想到搞政治的人说的做的和心里想的原来完全不一样。要知道林彪当时抓阶级斗争最狠,我早在长辈们(贫下中农)告诉的许多故事中了解到大部分地主富农原来都是靠勤劳,特别是节俭,成为地主富农的,有不少仅仅在解放前三年变成地主富农的,甚至说他们简直“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就成了倒霉蛋,“土改”对中国“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过于严苛的嘲弄,解放全国的“四类分子”——这是件多好的事啊,可为什么林彪要反对毛主席呢?
第四件事,一次当众和父亲的激烈争执后,父亲从此再也没有对我拳打脚踢过,我从此悟出一个道理:和父亲吵架一定要有人在场公开吵(哪怕只有母亲一人在场也好),否则,不但有口难辩,而且总是以挨打告终,就因为是父子关系一开始就无平等可言(后来才知道这是儒家文化“父为子纲”的精华)。这一点我非常喜欢的《毛主席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我早有一本油印本)中毛主席说到与他父亲毛顺生的抗争故事,最后反而争吵慢慢少了,遇事也有商量了。后来,我感到中国的官民关系,就是父子关系的政治延伸,所以,国民必须要自己组织起来。
第五件事,我一家住的猪圈位于村子的边缘树林前,经常有各种小动物出没,特别是那些可爱的松鼠真是招人喜欢,一次偶然发现一面墙头瓦下之间有四只还未睁开眼睛的光溜溜小松鼠,我把它们取下来天天用麦管给它们喂米汤,一个月后小松鼠就长出了小绒毛和漂亮的尾巴在床上蚊帐上耍欢,我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收工回窝与它们相伴,它们也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时光,可是,突然有一天早上醒来没有听到它们的叫声,也没有看到它们在蚊帐上蹦跳,急得我到处找也没下地去干活,最后在被子底下找到了它们,四只小松鼠直直地僵在一起,显然是深秋天气它们钻到被子底下取暖,给酣睡的我可能一下突然的翻身压得往窒息而死的,我不禁泪流满面,默默地把它们带到猪圈后面山上埋藏,站在那个小墓前,我深深感到欠疚,感到这世上美丽的生灵原来是如此脆弱,人与整个自然生灵的关系很可能也是同样脆弱,所谓改造自然很可能是完全多余的,恩格斯早就说过,人类每一次愚蠢而自私的对自然的征服都会遭受一次自然强大的报复和惩罚,因而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解问题,今天我遭受的惩罚就是心灵的阵痛,其实,我当初把它们取下来,母亲就说过这样松鼠妈妈会不高兴的,母亲是老庄哲学的践行者,认为一切都应当顺其自然,让它成为它自己(一如英国人说的Let it be!)。
1974年,由于农村生活的贫乏让我不堪忍受,逃到县城想学点什么手艺。戴着一顶破草帽,脸晒得漆黑,穿着一条补丁连补丁看不到原形裤子的我,遇到一位叫吴英的城市青年,他穿着漂亮,人也长得帅气,把我打量了半天说“你是哪里的?”我实话实说农村来的,他说“我怎么从你身上看不出一点儿农村来的影子?”,于是,吴英把我带到他家洗澡还换上他自己的衣服,他也成了我第一个城里的好朋友。后来在城里先后跟人偷学油漆工、贩卖水果等,但依旧是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里。
在赚到一张船票钱后径自到省城,想进中医学院学医并找到从杂志上看到的一位研究“药露”的教授家,他问我是不是赤脚医生,我说不是,因为我不是当地人没有资格轮到我,他说那你干嘛要学医,我说看到农民缺医少药所以我认识很多中草药给别人行行方便,他告诉我这条件上不了大学但精神可佳。于是送我一篇关于做“药露”的文章还介绍我去找一位老乡搭睡一晚,可这位工农兵学员老乡知道我的情况后简直吓坏了,说我这样到省城只会成为街上的流浪汉,他说了一句让我当时就愤怒起来的话,说“饥饿起盗心,现在城里对流窜人员抓得很紧,你赶快回乡下去,我没有办法帮助你”,我气得扭头就走了。
我一个人在八一大道瞎逛悠,偶然走进一家古旧书店,挑到一本“特价书”,是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写的《关于德国哲学与宗教的历史》的中译本,该书给我一种从未有过的特殊激动,从此着迷于哲学的思想解放力量。
其实,早在1968年我就在父亲的箱子里发现已被撕烂的半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当时翻过一下,只模糊记得一个比喻,大意说的是:春天到了,一棵种子发芽从地下钻到地面呼吸空气感受阳光是必然的,什么时候发芽钻出地面是偶然的,其他都没有印象。我闯入哲学王国似乎也是得之于这样的偶然。这回,无法形容海涅写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当时对我的吸引力。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哲学的魅力和哲学对人的解放力量。该书不仅详尽地描述了根源于德意志民族的泛神论是怎样最后导演了那场席卷全欧的路德改革,而且预示了德国古典哲学将把这个民族由分散的等级专制制度推入统一扩张、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的新世界。这一切,把当时还在躬耕田亩的我简直惊呆了。最后,我在书的末尾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哲学是人类创造天赋的催生剂,它给人以智慧和勇气,使人诚实而又机敏,它激励我们走出温室去拥抱未来的陌生世界,让我们超越现实书写历史,追寻可能的世界!
1975年春,住在猪圈里的我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中我身为毛主席的秘书,一天马克思突然闯进来暴怒,指着我的脑袋问:“毛泽东在哪里,你叫他给我滾出来,这哪里是我的思想?”我直吓得浑身发抖,赶紧一边说“尊敬的马克思,请您别生气,别生气,毛主席刚去WC,我一定转告您老人家的意见,毛主席非常崇拜您啊”,一边惊奇自己居然见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正要去搬毛主席坐的太师椅,只听马克思说了一句“那还差不多”,余怒未息,转身就不见了,我顿时吓出一身大汗,醒来才知道是做梦。
这梦让我感觉非常奇怪,那时,我和全国大多数人民一样对毛泽东崇拜得五体投地,更别说有半点怀疑,至今弄不明白在1975年的那个猪圈的春天里,为何会做这么大逆不道的梦!当时只告诉母亲一人,母亲非常担心,再三再四地叮嘱说:“崽俚,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1975年冬天至开春,还有一件“赶走监工书记肚里冒火”的事。那是我所在人民公社要盖新大楼,就从各个生产大队分别平调来80多个民工,组成一个基建队平整地基,我是其中的一员。这事由公社一名副书记和基建办主任(上山下乡办主任兼)负责,他们指定一名曾经做过大队长的姓江的人做队长,负责监督大家干活。可是这位江大队长对大家非常严苛,不但很少让大家休息,还克扣我们大家的伙食补贴,简直就是一个连环画小人书上看到过的旧社会手里时刻举着皮鞭的“奴隶监工”,民工们个个敢怒不敢言。一次,因为一位生了病的老大爷挑着沉重的土筐走得慢了一点,又遭到江大队长在后面训斥。经常业余采药行医为人看看病的我,实在看不下去,怒不可遏地上走上前去一把把他拉过来骂道:“你他妈的什么东西,天天催什么命?太不像话了,没看到他生病了吗?”可能是用力过猛,这位江大队长竟一下被摔在了地上,这时其他民工也都围上来,有人还在叫“打得好”、“那王八蛋实在不像话”。不料他从地上爬起来,竟吓得面如土色,没说一句话就钻出人群一溜烟跑了。后面有人叫“你他妈滾吧!”可是,那老大爷放下担子走到我面前,说:“年轻人,你这下为了我惹大祸了”。这事完全突如其来,我当时什么也没想。
晚上,果然X副书记、基建办Y主任召集民工大会,说“公社盖新大楼是加强党的领导,为子孙后代造福,钱宏目无组织领导殴打领导的错误,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破坏行为,必须受到批判和严肃处理。”我站起来说“白天我只是实在看不下去,可能一下用力过猛,绝没有打江大队长的意思,不过本着尊老爱幼的精神,他比我大,我愿意向他表示道歉。但是,本着毛主席‘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他也应该向这位老大爷道歉,人家的确是生病了”。这时,一位年轻民工豁然站起来说:“书记、主任来了也好,大家都看到了,这事完全不怪钱宏,他只是为人家打抱不平,不是为他自己。书记、主任可能不知道,江大队长平时是怎样领导的,他对大家简直比旧社会的恶霸还不如,我们被调到公社搞基建和去做水库不一样,生产队除了记几个工分什么也没有,感谢公社给大家每天三毛钱补贴伙食,也经常被江大队长克扣着,害得大家都吃不饱”。没想到,这一下民工们都纷纷站起来,炸了锅似的诉说这位“监工”的问题,书记和主任听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来说:“大家来公社平地基都很辛苦,我们知道了,就这样吧”。说完瞪了那江大队长一眼,两人转身就走了。第二天,那江大队长就悄悄卷铺盖走了,改由那位站起来为我说话的年轻人作民工头了。
我不久也离开基建队回村里去了,但心里一直非常感激那位年轻的农民朋友。事隔多年后(大约是1993年),父亲被选为县文恊主席,一次,他告诉我说,“县里开文代会时,碰到原来公社的X书记,他还记得你,问我‘你那个好倔好可恶的儿子现在到哪去了’呢,你当时是不是让他感到很头痛啊?”其实,那位X书记和Y主任当时就是父亲的朋友,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来如此脆弱,不管是为他人还是为自己,冤家真的宜解不宜结。
由于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能干的邓小平被再次打倒,使我感到非常迷惑不解,偶尔得到一本《邓小平言论选》(两校大批判组编),又被书中的世界惊呆了,书中不但有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指责的那些内容,还发现了邓小平先生对八路军讲话时,大量赞美蒋介石先生的话,这使当时的我陷入一团雾水之中,从此对“中国革命的真实历史及其各种风云人物究竟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开始发生强烈兴趣(后来1982年,读到五四名宿第一次党代会大会主席江西人张国焘先生的《我的回忆》,始知西安事变始末原由,更加促使我阅读了大量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资料)。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先生去世,我在田埂上听到广播后仍然不禁泪流满面,没有任何人要求,自己做了一个黑袖标并写上“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垂不朽”戴着。10月从友人李晓岗先生处听到所谓“四人帮”被抓后的种种消息和传闻,感到这世道将有大变!
1976年初,由于父母回城恢复工作,我由随父母下乡的“务农青少年”转为“知识青年”身份,这是一种曾经渴望得到的身份。1977年进入高中生扎堆的“北山知青场”,不久赢得“老大哥”的绰号。
同年底,给国务院写《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考察报告》,认为1968年知青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与延安时期有本质区别,延安时期的确收到“思想改造”之功,而“知青”,则始于对当时城市造反派的惩罚、贬黜,终于减轻“非农业户口”人口就业压力的常规措施,结果不但知青们无所作为,还造成大量人力资源浪费,农村公社和农民更不欢迎,因而必须结束该“运动”。至次年即1978年6月,竟收到国务院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回复信,告之将于年底召开全国会议统一解决。同年,看到友人马超英一家三兄弟同时考上医科大学,想到国家将有大批正规医生走向社会,因而放弃了当医生的想法,并终止了业余采药行医的行为,兴趣点完全转到哲学和社会发展的思考上。
还有一件事,就是看美国故事片《音乐之声》和《哈里之战》后,我突然感觉自己本性上不是中国人。还有后来看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我发现人其实无所谓好坏,再“坏”再“强”的人,心里都有柔软的一面,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自组织能力与外连接平衡力,所以,关键是看用一种什么的组织方式,去实现一种什么的价值目标。心理过于刚硬又自我中心的人,实际是一种病态。这三部电影似乎把我内心的某些东西给唤醒了。
1978年11月,由于知青场领导看到国务院的回信,加上我干活卖力尽责,当年还成立一个由我为组长的科研小组,搞“水稻杂交育种”和“瓜果立体套种试验”(这个过程让我学到了很多生物化学常识),得到都昌县革委会全县通报表扬,还和知青场领队老师一起出席了县委党委扩大会议,直接向县长(革委会主任)书记汇报情况。于是,我被派到县委党校参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习班,并成为学习骨干,有幸读到李一氓、于光远两位先生赴瑞士和南斯拉夫的考察报告,及安徽、四川农民分田到户搞承包的调查报告。当时,已经流传一句“要吃粮,找紫阳;想吃米,找万里”的民谣。学习班结束时,校长竟让我代表党员作学习心得总结发言。
我总是有点想好了就立马干的傻劲。12月回到所在“北山知青场”,当即鼓动场领导把知青场60多个人分为农业、林业、副业三个专业生产队(分队过程引发一场不小的争吵风波,平时玩的好的朋友也红起脸来,大家都欢迎改变,但当时改变关键在于,谁都不愿意到农业队,而农业队偏偏需要最多的人,但终归没有酿出大事),实行工效分配挂钩。结果,次年即1979年底算账,收到显著效果——由原来全场每天10个工分满分合0.12元,猛增至最高林业队达1.97元(我为林业队队长),副业队1.36元,最低的农业队也达到0.89元,尽管这一年知青场大部分“知青”通过各种途径陆续返城工作(1978年底开过上山下乡工作会后1979年再无新知青下来),但三个每个队都有一位老农民负责组织生产。
但是,1978年的学习和改组知青场劳动生产结构及分配方法的操盘过程,给了我思想和精神上很大的激励。
于是,一个沉思青年,经过中国长辈文化谦卑和虚心的潜默教化与中外圣哲的思想激荡之后,在“广阔天地”历练成长,竟自开始有了言说的冲动——也许,这是中国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收获的一颗不被人注意的小小果实,尽管,这果实里孕育着什么样的种子,是一粒种子,还是一把种子都尚不清楚!
1979年秋天,我回县城恢复“商品粮非农户口”,进入教育系统工作。经过县文教局两个月的培训,便走上课堂,由农民、知青转变成“人民教师”身份。一次县镇教学例行巡回检查的公开教学后,上面领导告诉我:“你可以教中学了”。于是,我仅教了半年小学四年级语文,就匆匆走上中学讲坛,同时,承担起几个不同年级的政治、生物、音乐、地理、语文五门课程的沉重教学任务(单是一次需要批改的作业就达219本之多)。但我心里想的事情,却与这份职业完全无关。
1980年春,着手写作《论社会生活发展动力之动力》,该文长达5万余字分三个部分。
1980年春,着手写作《论社会生活发展动力之动力》,该文长达5万余字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哲学,引用大量自然科学(如相对论的“同时性原理”、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等)和社会科学知识,提出“实体辩证法”的概念,认为不管哲学家们用什么方式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都必须置身(人自身及其工具)世界之中直面真实本体(人的心身、生活和社会生产),真理的权威性与哲学家个人的权威性只能来自于与真实世界永不间歇的互动过程之中,所谓真理,也只存在于这一互动过程中偶然显现的某个平衡点上,因此,所有真理,都注定是相对的、暂时的和平等的,而不具有永恒的逻辑演绎价值和历史实践价值。
第二部分,是“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认为专注于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人们,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任何历史阶段都可以通过强行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整体损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平衡,从而最终付出既无社会效率、更无社会公平的惨痛代价,因此,文章明确反对把官办经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直接等同于公有制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传统观念——源自于苏联军事斗争需要和尽快完成战胜所谓资本主义国家而准备物质基础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因而为了实现经济超高速发展,以“剥夺农民和民族资本家私有财产”、“高度国家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等一系列方式方法,进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提出不管是国有制经济还是私有制经济,都要以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为目标,国家、个人和集体拥有财富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社会整体财富增长才是关键”的经济观,提出借鉴清末洋务运动后期从“官商合办”、“官督民办”,到慈禧新政和民国初年的完全“民办”(那时,政治上虽然动荡不定,但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辉煌的时期)的历史经验,认为只要社会整体财富增长,就符合“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第三部分,是“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人文社会主义”概念,认为过去的子民、国民,都不等于现代公民,国家不等于社会,因而国家主义不等于社会主义——《我的奋斗》、《第三帝国兴亡史》和《勃列日涅夫的力量与弱点》等书中描述的生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中国式的法律、法制与始于孟德斯鸠“法即规律”的现代法治秩序无关,因此,始于儒家的“以民为本”、法家的“以法治国”、道家的“以德治国”与现代文明的民主自由、法制秩序、道德规范有本质区别,最后,文章坚决反对始于蒋介石先生无限推迟“宪政”出场的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犯下的最大罪恶,不是烧杀抢掠,而是打断了中国的近代化历史进程,使我们真正成了“灾难沉重的中华民族”。
该文完全模仿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的结构和文风,有一定的幼稚性,如“实体辩证法”的提法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式的表达方法——我对只念过中学的恩格斯情有独钟,当我从《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读到爱因斯坦回复伯恩施坦关于《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出版价值的信中说“如果恩格斯不是这样一位名人,我看不出有很大出版的必要”,多少有些伤感。因为在我看来,恩格斯的机智与悲悯之心在该书中得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且,恩格斯是把“自然-社会-文化-心理-历史”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纳入人类理论思维视野的第一人,如他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解问题,是对康德和黑格尔纯粹思辨推导的超越,他的著名论断:“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也许对于科学昌明的西方人,特别是对于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理论思维巨人来说没有多少信息量,但对于“爱因斯坦现象”(如所谓“思想实验”)来说,仍然是成立的,特别是对于东方世界的中国人来说,则恰恰是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只可惜我们中国至今还在谦卑地甘当古人和权威,尤其是政治性权威的思想侏儒。
后来成为《人民日报》名记者,写作过《乒乓外交始末》等大量报告文学的钱江先生,是我的《论社会生活发展动力之动力》的第一个读者,当时钱江先生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学习,他把该文交给学校化学系和物理系的同学和老师阅读后,前后给我写来两封长信,表示赞扬和鼓励说“我和我的同学,不止是中文系的同学,还有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同学和青年教师,对你的探索精神和探索成果十分钦佩和赞赏。在你面前,有着如此良好学习环境的我们感到很惭愧”。但是,不管怎么说,《论社会生活发展动力之动力》一文的写作,是我在八十年代以前思考哲学问题和中国社会问题散点思考的一次初步的具有整体性的总结。
1981年夏天,应《读书》杂志编辑包遵信先生之约作长文《鲁迅:中华人格的光辉典范》。给东北师范大学沈正衡副教授写长信,批评他写的《自然辩证法论纲》中的一些错误之处,收到作者长达10页纸的回信,大意是完全接受并自己剖析我所指出其《论纲》中三处大的错误和原因,最后建议我一定要上大学,可以考虑直接上研究生。沈教授的回信让我的自信大增,一是从他里证明我是有思想力的,一是他的字写得甚至连我这拿锄头的手也不如,心想,原来字写不好也能当教授啊!
1981年底,我给胡耀邦先生写信,表达两个意思:一是认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应当那么快就结束,因为讨论才触及问题的表象,远没有达到提升中华民族“理论思维能力”的目的;二是当时听到要把华国锋搞掉的传闻,我非常反感,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政治体制,是英国光荣革命后和二战后的的“虚君立宪内阁制”,如果保留毛主席选定的华国锋“准虚君象征性地位”,华在位又虚位,既能凝聚人心,又没有人抢夺最高位相互倾轧,可以减少权力斗争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内阁制政府的好处,就是不行就换,可以保障和增强社会的活力。所以,如果搞掉了华国锋,中国很可能错过一次通过“社会和解”(全面解脱“四类分子”很好,已经倒不了乱的“四人帮”也应该放了,回归社会,告老还乡),结束两千治乱循环(改朝换姓)的历史机会!写完,还到县邮局挂号寄出,事后感到这行为有点幼稚,但并不认为我的想法幼稚,当然,这涉及中国政治人物格局和历史感问题。
1982年春,我带着简单的衣物和满袋子的手稿,借着报考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守昌先生研究生之名“离教出走”,心中响着列宁《纪念欧仁·鲍里埃逝世25周年》中的一句话:“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可以凭国际歌找到真正的同志和朋友”,我已经完全相信,凭着自己的思想,就能找到真正的同志和朋友!偷偷作小诗一首:
春夜,我听得地下
有躁动不安的声响,宛如
美妙的天籁和音
牵动我根根神经
哦,那分明是
野草
或许还有乔木的
种子
在悄然萌动……
蓦然间,有样东西
潜入我的心田
它,抖颤着身子,仿佛
催逼我
立马加入那天籁和音
叫我再也难得
安宁
于是,在那个看似凝静的
月夜
我走出了故园……
编辑同志,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但既然收到这个邮件,并问到知青的生活,我想我应当回答。不管你们喜不喜欢,我只是一种真实记录。
后来,我也未能走上“高考改变命运”之路,当然,我也就自然不是学者,且现已出“官场”和“商场”,但依旧一如既往,想得多,干的也不少,我的写作也是干的一部分(告诉别人我看到了什么,想了什么,要干什么,明人不做暗事),不管成功与失败,我都喜欢,我总是体验到生命跨度的现在进行时!
祝你们好运,呵呵!
顺致敬礼!
钱 宏
全球共生论坛(GSF)发起人
2012年8月3日于北京邮电大学心约居


上一篇: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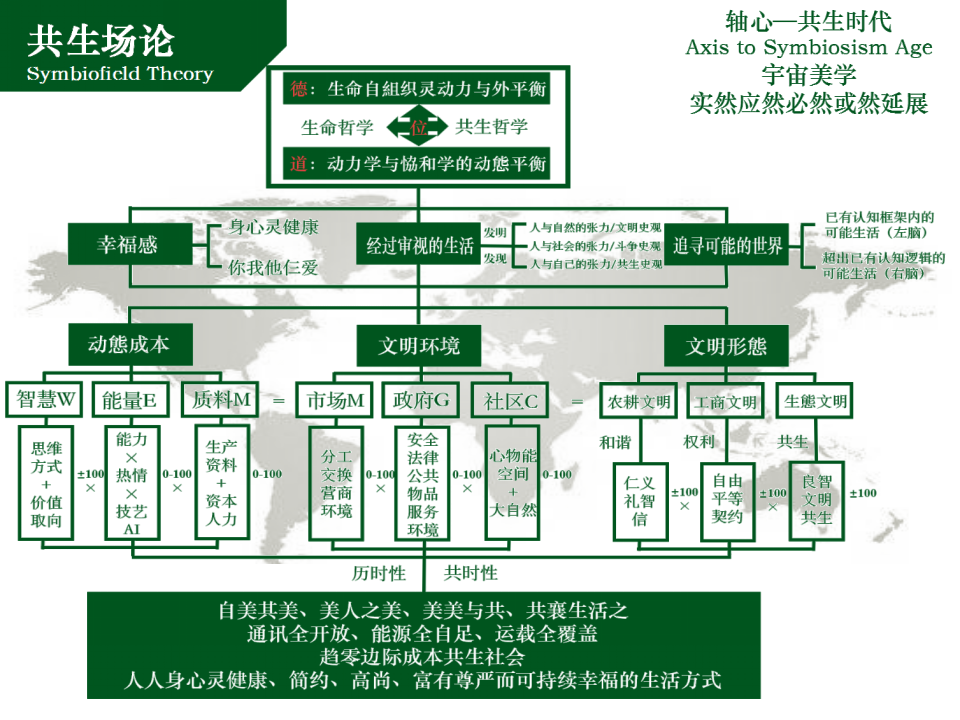





寒年路甜玉興
知青之謂意无家
緣去缘来皆安昂
天真幼稚憑傻勁
何可得失非权衡
愛通乾坤思千載
有道无道間道成
乘桴浮海觀世界
孞烎言必稱共生
2022年1月1日于Vancouver
2022年01月02日上午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