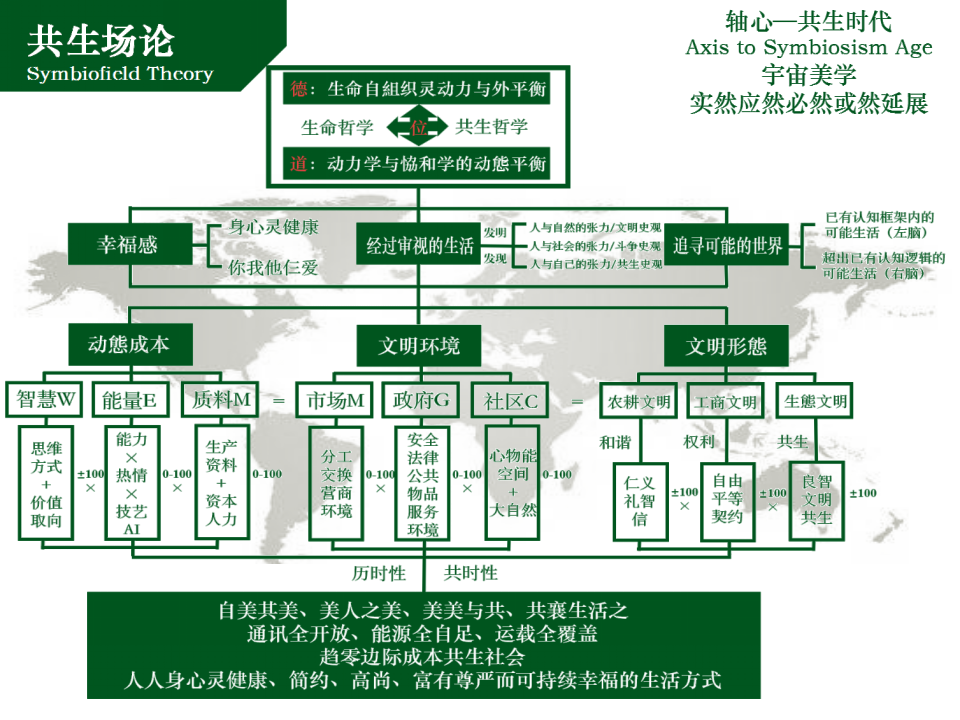New Articles
-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2026/02/24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2026/02/24【共生经济学·前言】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The Cognitive Bias and Fragmentation of Economics as...
-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2026/02/22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2026/02/22《共生经济学》自序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How Should We Face the “Ultimate Free Lunch”? 一、从宇...
-
 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2026/02/17
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2026/02/17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Modern National Normalization under the Global Symbiotic Paradigm ...
-
 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2026/02/16
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2026/02/16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Chinese Reproductive Officialdom: Why Regime Change Has Not...
共生思想理论前沿
THE THEORY
-

-

-

-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Symbiosism:Charles Thomas Taylor &Qian hong又一次量子缠绕...
查看详细说明
Speech
-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 ——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钱 宏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语从金音玉(Yǜ):金口玉言,一诺千金,性人诚恳、执信; &n...
-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点击播放 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访钱宏主持人:...
“一座自我言说的语桥”——悼念李泽厚先生仙逝!
发布时间:2021/11/05 公司新闻 浏览次数:647
“一座自我言说的语桥”
——悼念李泽厚先生仙逝!
钱 宏
易中天《盘点李泽厚》,“绕着说”,这个说法很逼真!
“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冯友兰1986年给李泽厚先生的题词,静静地挂在先生北京房子厅堂里。

我只要了李泽厚先生一本书,当然是《美的历程》。他给我签名时,问我为何只要他这一本书,我说先生著述甚丰,我相信一定会有一本能够留芳百世。
先生问为何是这一本?
我答: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美的历程亦当是精神的超拔和思维的创新,先生通过中国艺术品的代际呈现,将华夏美学的挣扎和扭曲,酣畅淋漓地发挥出来。
时至今日,镜鉴着中国精英们处事处世曲折迂回绕来绕去,却依然跳不出“华夷之辨”“犬儒逐利”的现实人生宿命,以致左右难逢源,东西皆不伦,您象一只东方的夜莺,在暗夜里呼唤美的——精神自由思维创新——回归!
对我们这些从“文革”幸存,进入城市社会的一代思行者来说,李泽厚先生无疑是承前启后者,是“一座自我言说的语桥”啊!
我知道,我的回答,先生未必认可。先生听完什么也没说,只是遗憾地望着我微笑!
作为《国学大师丛书》(1991-1996)的总主编,《追寻可能的世界》(1989)和《共生:一种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2021)的作者,我深知,“美的回归”,在故园,依旧只是一种奢望!
孞烎2021年10月4日记于Vancouver
又及:
想起一段往事,照录于此。1991年初,为了组织《国学大师丛书》,我四处寻找支持帮助,也有主动找我理论的。这些朋友中,就的李泽厚先生的弟子刘东博士,巧的是,他也是包遵信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副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中《西方的丑学》一书的作者。
刘东找到我,是告诉我,以李先生的名望,《国学大师丛书》必须有《李泽厚评传》,否则《国学大师丛书》就会留下一大缺憾,而且,他本人就是《李泽厚评传》的最佳作者。但当时,我和张岱年先生讨论这个问题,为入选丛书立了一个原则,叫“生不立传”。刘东听后,真的感到很遗憾,我说,你就当感到开心才对啊,李先生身体好是好事啊!但同时,我也想到了东方《美的历程》,从缺失精神自由与超拔上看,其实也可以叫《东方的丑学》!当然,我不能说出来。
2016年,我与李中华教授在北大高等人文学院重逢,他提议可组织《国学大师丛书》续集,我想,如果现在有人出资襄赞此事,我是乐意继续为作者们做嫁衣的,那么,当然有《李泽厚评传》!
其实,当年做《国学大师丛书》是有遗憾的,原计划出版36种,结果因故只出版了28卷,象《黄侃评传》、《陈垣评传》都未能完成……
盘点李泽厚
实在的说,当我听到这个真实的“笑话”时,却有些笑不起来。没错,李泽楷与李泽厚,只不过一字之差,看走了眼也不足为奇。问题是,他们当真是看走了眼吗?未必。说白了,这些学生之所以把“李泽厚”看成“李泽楷”,只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李泽厚。
于是,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世事的苍凉。
想当年,李泽厚的人气多旺啊!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几个不知道李泽厚?就连他那本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
有人甚至宣称,以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这话也许夸张了一点。但不管怎么说,当年李泽厚的知名度,决不亚于今日之李泽楷。然而今天的大学生,已大多不知李泽厚为何许人也了。老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白云苍狗,本是当然。但,从八十年代初到如今,不过二十多年光景,无乃过速乎?
我终于没敢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李泽厚。毕竟他是我所敬重的前辈,何况我也是所谓“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中之一员。面对面的,实在难以启齿。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出来。因为这已不是李泽厚或李泽楷个人的事。正如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比尔(盖茨)不知道保尔(柯察金),并非比尔或保尔个人有什么是或不是,实在是时势所使然。何况这个并不好笑的笑话背后,也不乏耐人琢磨的东西。
其实,就连我们这些人,现在也不怎么读李泽厚了。李泽厚出了新书,《世纪新梦》、《论语今读》、《己卯五说》等等,也买,但未必读,读也不激动,更没有当年那种如饥似渴先睹为快的感觉。我们买李泽厚的书,毋宁说是“怀旧”的成分多于“求新”。更多的,是出于对他的尊敬和怀念。是的,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李泽厚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是,无论我们当年或现在是否赞同他的那些观点(事实上也从来就没有全部同意过),我们都不能也无法否认他对我们的影响。毕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李泽厚是重要的,他的影响也是抹都抹不掉的。
这样一个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物,为什么转眼之间就成了明日黄花?是李泽厚变了,还是我们变了,或者是时代变了结果李泽厚和我们都变了?
这倒是应该也值得弄清的问题。
因此,我决定“盘点”李泽厚。为我自己,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
不过,李泽厚的影响超出学科范围,真正成为一代青年学人的精神偶像,却是在八十年代初;而他的崇拜者、追随者、赞同者、欣赏者和心仪者,则主要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同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没有比这一代人更倒霉的了。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长知识的时候没有书读,最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去了农村,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时已是“老大徒伤悲”。以后的情况也十之八九不如意。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总算能够在已为人妻人夫甚至已为人父人母时,才又重新回到课堂。这就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又很幸运。我们接受中等教育是在1966年前。那时学校里推行的,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应试教育”。学生的升学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有时间阅读大量的课外书。这是其中许多人在恢复高考后,能够以“同等学力”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后来,在运动中,在农村里,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滚打跌爬,历尽磨难,茁壮成长。有的炼就“金刚不坏身”,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艺”,有的已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的则更加是“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更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就在我们走进校园不久,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号召,邓小平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我们这些刚刚从社会底层浮出水面的大龄学生,几乎天然地与之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合。陈旧的知识早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陈腐的说教更让我们顿生厌恶。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回到讲台上的大学老师们,立马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学生。
这时,李泽厚来了。
李泽厚来得很潇洒。
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不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位思想家。他拥有的财富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学”,而是“思考”。他甚至没有什么“专业”。哲学、美学、社会、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领域;历史、政治、文学、艺术,都是他研究的范围。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思想文化史。他的三部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影响深远,《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意义非凡。相比较而言,他的《美学四讲》、《美学论集》反倒显得单薄。在他的美学著作中,我认为只有《美的历程》是不朽的,尽管他自己更偏爱《华夏美学》。
李泽厚抓住了这个机遇。因为他是有备而来的。
诚如骆玉明教授所言,李泽厚是在那个荒唐年代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并且从事着文字撰述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连续地在社会中造成震动,并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也就是李泽厚一人而已。
于是,李泽厚便光芒四射地表现出他的魅力。
被视为“中国美学史外编”的《美的历程》一书,起先曾以《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札记》为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美学》(第二期,1980)上发表了前三章。初刊之日,便广为传颂,纸贵洛阳。读者盼其全书,如久旱之望云霓。次年三月,该书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后十年之内印了八次,后来又有了多种版本(比如广西师大社的插图本),无疑是学术著作中最畅销的。即便现在看,它的“含金量”仍然很高。因为它不但跨越五千年历史,贯通多种艺术门类,而且“兼具历史意识、哲理深度、艺术敏感,还颇有美文气质”(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样的著作能有多少呢?凤毛麟角吧!
以十几万字的篇幅来完成这样一个“美的历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且能做到该细密处细密,该留连处留连,丝丝入扣,顺理成章,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巡礼中触摸到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诚非大手笔而不能为。但最初打动我们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它的气势和情调。这就像是欣赏艺术品。当我们刚刚接触到一件雕塑、一幅绘画、一个青铜器或一首乐曲时,我们是来不及仔细琢磨它的。我们很难一下子体会到它的深刻含义,也不可能马上把它的形式结构看清楚。所有这些,都是以后的事,而且也许需要反复欣赏、反复体验、反复品尝、反复咀嚼,才能“品出味来”。而在当初,在与艺术品猝然相遇又怦然心动的那一刻,我们总是“一下子”就被感动和震撼了。我们分明感到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在吸引和呼唤着我们。《美的历程》便正是这样。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它的魅力,正在于它的“说不清”。
的确,这是一部说不清该算什么的著作。专论?通史?散文?札记?都是,又都不是。它是一个鸭嘴兽,是兽也是禽;它是一个猫头鹰,像猫也像鹰。你还可以说它是个“四不像”,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但你无法否认一点──它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
与众不同,正是《美的历程》使我们心仪之处,也正是李泽厚使我们心仪之处。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与众不同”的。它需要胆,需要识,还需要才。有胆才敢做,有识才能做,有才,才做得出、做得好。李泽厚恰恰正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美的历程》一书真是写得英姿勃发,才气逼人。单是标题,便气度不凡: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魏晋风度、盛唐之音,更不用说每过几页就有一段华彩乐章了。实际上,《美的历程》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它充分地表现着李泽厚的艺术魅力。
但更重要的还是胆与识。
我在《闲话中国人》等多部著作中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要求“大家一样,人人有份”则几乎是中国人的“集体文化无意识”。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乃是做人的大忌。只有历史上数得着的那几个顶尖级的大英雄大人物,才敢如此。但即便是这些大英雄,一开始也要受排挤、遭非议。直到后来,他们成了众望所归公认的领袖,与众不同才不再成为问题。
大英雄可以与众不同,不等于别人也可以。恰恰相反,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六亿人民就连衣服都穿得一模一样了,何况写文章?那更是必须一个模式一个腔调,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李泽厚是什么人,也敢与众不同?显然,这就必须有足够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力量来支持。不少人指责他的一些结论过于武断。但武断的背后,又何尝不是自信,以及敢做敢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断”也不容易呢!就是借给你一个胆子,只怕也不敢。正是在这里,在“武断”和“狂妄”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了李泽厚的人格魅力。
但仅仅如此显然不够。时间毕竟已进入八十年代,敢于标新立异的人多起来了。社会上的那些“问题青年”,就胆敢身著“奇装异服”,穿喇叭裤,戴蛤蟆镜,提收录机招摇过市,能说他们也有“魅力”?真正具有人格魅力的人,背后必定有理想和信念来支持。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事实上李泽厚之所以会把他的文章著作写得与众不同,从根本上讲就因为他的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就在1981年,李泽厚在回忆起自己的读书生涯时,便夫子自道,说他“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走我自己的路》)。这其实也就是李泽厚文章著作的特点:决无陈词滥调,决不人云亦云,新意时见,新说迭出,充满新鲜气息。唯其如此,他才在表现出人格魅力的同时,也表现出思想的魅力。
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果不其然,他那篇《走我自己的路》刊出后,“一位标榜人道主义的善良领导”便紧张兮兮地跑到他家里对他妻子说:“怎么能用这种标题?这还了得?”
是了不得,因为年轻人听进去了。五年以后,这句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也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格言,到处出现,谁不说谁不够“品位”。就连小品节目中的人都会说,只不过被说成了“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或被改成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的去吧”。
是啊,人生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要么走别人的路,那就只能让自己去说了。李泽厚不愿意让自己去说,他选择了走自己的路。
李泽厚是一个先行者,他走在了前面。
跟在后面的,是崛起的新一代。
现在再来讨论前面那些提法和论争的是非对错,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事实上,李泽厚的许多观点和提法,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普遍的认同。争议一直存在,而人们的认识则在前进。但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并不重要。或者说,这很正常。马克思说过,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思想家并不一定非得别人同意他的观点,而只希望能够启迪智慧。
李泽厚的意义正在于此。
李泽厚是一个在学术界大多数人还一片茫然时筚路蓝缕的人。那时,学术界刚从十年动乱的重创下醒过神来。一些人心有余悸,许多人严重失语。不要说做学问,连话都不会说了。甚至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帮”的腔调。这是一种连“党八股”都称不上的话语模式,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了无生气,乏味透顶。这种人人憎恶的文章套路之所以还能延续一段时间,除习惯使然和一些人胆小怕事外,也还因为大家不知道,如果不这样说话,又能怎样说。
开始时李泽厚也一样。他也写了诸如《实用主义的破烂货》(1979)一类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改弦易辙了。李泽厚1980年的文章便已让人耳目一新。甚至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便已是纯正的学术著作,全无八股腔调。同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亦然。不过两书均嫌太过“专门”和“学术”,其影响便不如《美的历程》。《美的历程》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和朦胧诗一起,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
如果说,朦胧诗让我们知道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甚至就该这么写);那么,李泽厚则让我们明白原来学问还可以这样做,甚至就该这么做。比方说,讲哲学,并不一定要套上唯心、唯物之争;讲文艺,也不一定要套上现实、浪漫之别。然而在此之前,这种套路是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结果就闹出很多哭笑不得的事情来。比如李贺,照理说只能算是“浪漫主义”的。又因为李贺的诗“鬼气”太重,便只好算作“消极浪漫主义”(李白则是“积极浪漫主义”)。后来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他老人家喜欢李贺。这下子文学史家们就狼狈了。伟大领袖怎么会喜欢“消极”的东西呢?只好另找证据,证明李贺其实是“现实主义”诗人。那么李贺究竟是什么“主义”?什么都不是。中国文学史,根本就不能那么讲。李泽厚不这样讲,也就无此尴尬。这在当时,却不能不看作一个“重大突破”。
但李泽厚的意义还不仅于此。
就我个人而言,《美的历程》以及李泽厚的同期其他著作让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人,为什么要有学术研究,为什么要做学问?李泽厚的实践告诉我: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人生。也就是说,为人生而学术。因此,一个人文学者,就应该把学术研究和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的遗产当作鲜活的对象,把做学问、写文章、出版著作变成自己生命的流程。《美的历程》就是这样做的。比如“苏轼的意义”一节,讲到苏东坡写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挂冠服江边”,却不过回家睡觉,并没有“拏舟长啸去矣”时,李泽厚说:“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脱人世这个大罗网。”如果没有人生的体验,这样精辟的话岂是说得出来的?
历史的遗产一旦被看作鲜活的对象并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相结合,就成了活生生的东西,也就不会有尸臭了。过去(也包括现在)一些学者专家教授流的文章之所以那么僵硬呆板枯燥无趣,味同嚼蜡不堪卒读,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字表述能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看作活物。他们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时把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哀莫大于心死。心已死,文字还能活起来?
学术著作变成木乃伊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这些学者们总在说别人的话,至少是总在用别人说话的方式在说话。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人生而学术,而是为某种现实的利益而学术。这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是否符合公认的“学术规范”和“量化标准”,小心翼翼地不要触犯了学术界的“规矩”。这时,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别人用什么方式说我也用什么方式说,无疑是最保险的。而当所谓“学术规范”其实不过“八股套路”,所谓“量化标准”也仅仅只是论量不论质时,大量炮制八股文章甚至学术泡沫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表述方式,而是一个“为什么而学术”的问题。为人生而学术,就要讲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总之,你完全可以不必顾忌任何成规陋见,不必死守某种模式套路,信马由缰,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才气和知识准备了。
李泽厚有。于是李泽厚便用自己成功的实践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通百通。从此,我们的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目光锐利了,思路敏捷了,就连文笔也变得流畅了。这都得感谢李泽厚。没有他,我们当真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这是一种智慧的启迪。许多人甚至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寻。
但同时,李泽厚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得鱼忘筌,得兔忘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河,李泽厚老师不必再为我们摸石头。我们会记住他这座桥的。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实话实说,随便找个中学生,也不会写成这样!王朔有云:一盘菜,不必都吃完才知道好坏吧!《华夏美学》的开头如此,后面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我从头到尾都读完了。而且,由于当时买不到书,还做了笔记。
不可否认,《华夏美学》中仍有不少让人怕案叫好的东西,也不难看出李泽厚在撰写该书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已比撰写《美的历程》时系统深刻。如果要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华夏美学》倒是不妨一读的(但我以为读他那三部“思想史论”更好)。问题是李泽厚之所以是李泽厚,就因为他比一般研究者多了一份才气和灵气。然而《华夏美学》一书却灵气全无,就连书名也显得呆板俗气。开头不好,结尾也不好。结语那句“是所望焉”在《美学文丛序》中已经用过一回了,现在又用,岂非没了招术?
古人云,人生有三大悲哀:美人迟暮、英雄末路、江郎才尽。1989年的李泽厚,即便没到那个份上,也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华夏美学》出版后,几乎悄无声息,初版也只有区区5000册,与《美的历程》真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我就在心里惊叹:先生莫非老了?
随便翻翻1996年的《世纪新梦》,就能感觉到李泽厚的老态。洋洋42万字的集子,实在新意无多,就连作者自己也承认“内容和词句上都有大量雷同之处,因为翻来覆去也就是讲这么点意思”。其实,事情并不完全在于是否一定要有新内容。一些观点,尤其是一些基本观点,确实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复讲。问题是即便重复地讲,也可以讲得不重复。即便再三地讲,也可以讲得有新意。至少,你总可以讲得有趣一点,好听一点吧?然而我们终于失望。只有那篇痛快淋漓的《后记》,才让人觉得李泽厚宝刀不老。
还是回到《华夏美学》。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李泽厚对这部相对而言并不多么出色的著作情有独钟?他自己解释说“这可能是由于自己偏爱哲学的原故”,而“《华夏美学》涉及的哲学问题,比《美的历程》要多”(《华夏美学》日文本序)。也就是说,李泽厚的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哲学情结”或“哲学家情结”。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李泽厚的历程就多了一份理解。
李泽厚其实是想当哲学家的。在他放弃了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可能就有了这个念头。否则,家境贫寒的他,何不去选择一个既轻松又能挣钱的专业?他难道不知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然而当哲学家并不容易。在当代中国要当一个哲学家,就更不容易。你得选好自己的路。冯友兰先生就想过这个问题。他说搞哲学通常有两条路。一条是“照着说”,这是哲学史家的做法。另一条是“接着说”,这就是哲学家了。
李泽厚要“走自己的路”,就既不甘心“照着说”,也太愿意“顺着说”。然而一时半会的,也还不能“接着说”,便只好“挑着说”、“绕着说”。所谓“挑着说”,也就是拣那些相对而言可以“由着说”的话题,先说将起来,最后绕到最想说的领域里去。
李泽厚选择的是美学。
选择美学是对的。李泽厚原本就有艺术气质,内向、孤寂、忧郁而易感,又从小喜欢文艺,兼具哲学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艺术家敏锐的感受能力,搞美学是再合适不过了。更重要的是,较之哲学的其他分支(哲学原理、伦理学、认识论等),美学离政治最远,受政治的干预和影响最小,自由空间也就最大,但又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七绕八绕,还是能绕回哲学来。所以,先讲美学,再讲哲学,通过美学来讲哲学,应该说是行得通的。
李泽厚的“策略”大抵如此。事实上他的历程也正是这样:先以美学研究成名,同时进行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某些专题研究,最后则“直捣黄龙”。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三十年间,李泽厚一定阅读了大量的图书,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进行了反复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下过苯功夫”)。唯其如此,他才能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大放异彩。我们看他那时的著述和言论,真可谓四路出击八面威风:评康德,论孔子,谈文化,说思想,臧否历史人物,指点当代文坛,梳理古今脉络,畅议中西学说,直至最后建立和提出他的“主体性哲学”。其范围之广阔,气势之恢弘,见解之精辟,文笔之华美,让许多号称“美学家”乃至“哲学家”的人相形见绌黯然失色。
然而,就在李泽厚风头正健时,批评也同时群起。
批评来自两个方面,两派的意见也正好相反。一派斥其“离经叛道”,一派怒其“僵化保守”,但不喜欢他,则是一致的。李泽厚夹在当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正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李泽厚提起,也只能说“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这其实是一种无奈。
无可奈何花落去。曾经处于巅峰状态的李泽厚,终于走向了自己的末路。
本来,如果李泽厚只是在美学范围内自说自话,也没什么关系。美学毕竟是一种“虚玄之学”,随你怎么讲,圈外人都不会多当真。然而李泽厚是不甘心只当美学家的,也很愿意发表他对历史进程和未来走向的看法。这是他站在哲学家的高度,居高临下俯瞰历史得出的结论,不吐不快。这就实际上是在参与政治干预现实了。而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他的内在矛盾便暴露无遗。
就说“西体中用”。
这个说法,是李泽厚的得意之笔。从学理上讲,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中西体用之争的结果,也无非是四种选择:固守国学、全盘西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固守国学守不住,全盘西化行不通,中体西用早就声名狼藉,剩下的选择,也就只有“西体中用”。
问题没有,麻烦却多。
麻烦就在于究竟什么是“体”,“西”又是什么意思。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李泽厚自己认为已经说清,其实别人听不明白。比如,他说“体”只能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至于“西”,则主要是现代化的意思。现代化虽然不等于“西化”,但现代化之种种,包括思想、观念、方式、载体,却又都从西方学习和引进得来,因此无妨谓之“西”(《世纪新梦》)。也就是说,只要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现代化了,就是“西体”。这倒是不错,但用不着李老师来讲来教。因为我们早就穿牛仔裤、吃麦当劳、开进口车、用电冰箱了。一句话,我们早就“西体”了。只是不知道如何“中用”,用进口收录机放音乐打太极拳算不算?
看不懂的地方还很是不少。比如,李泽厚斩钉截铁地说,“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是“体”,“体”只能是“社会存在”;却又说,“学”既然生长在“体”上,并产生、维系和推动“体”,就当然应该为“主”、为“本”、为“体”。因此,所谓“西体中用”,又仍然可说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个“西学”,不但包括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其他理论学说,以及科学技术、政经管理等等(《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这可真是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体,既是“社会日常生活”,又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它还同时也就是“西体”),到底是哪个?西,既是现代化,又是新思想,还包括科学技术,又到底是哪个?
都是,也都不是,全加在一起才是,却又只能分开来说,而且越说越说不清楚。因此李泽厚这个提法就麻烦多多。如果“西”即现代化,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现代为体,传统为用”;如果“西”即科学技术,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科技为体,人文为用”;如果“西”即马克思主义,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马列为体,儒学为用”。这倒可能是李泽厚的真实想法。晚年李泽厚津津乐道的课题,是要把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或者说,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去夺取和占领“新儒学”的阵地。我想这大约又是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事情。海外那些“新儒家”并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国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未必领他的情,至于年轻一代,则恐怕根本就没有兴趣。
不能说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完全没有道理,更不能说他不是一番好意。他其实是很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一条康庄大道的。无论如何,这种想法令人敬重。他设想的蓝图也很不错:以社会存在(即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为本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科技生产力为关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既学习西方经验,又弘扬民族传统,以期平稳健康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有什么错?差不多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思了。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理论,还要那个含糊其辞歧义甚多的“西体中用”干什么呢?何况还要解释老半天。
李泽厚曾用孔子和佛祖的话来为他的《世纪新梦》作结,我也借来结束本文吧——
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佛云:不可说,不可说。
那就不说也罢。
- 今夕何夕
Pinned
- ZCM易中天
(Author)
- 石皓天
- 桃之夭夭
- 逆旅行人
- 傅建喜
- 千思
- 天籁🎞
- 吉
- 水龙吟
- 略
- 张杰
- 印枭
- 小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