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Articles
-
 AI三大瓶颈及其10个“傻白”和5个“傻精” 2026/02/04
AI三大瓶颈及其10个“傻白”和5个“傻精” 2026/02/04AI三大瓶颈及其10个“傻白”和5个“傻精”The Three Major Bottlenecks of AI and Its “10 Naïve Blind Spots” and “5 Cunnin...
-
 共生场图灵测试 (SFTT)的设计 2026/02/03
共生场图灵测试 (SFTT)的设计 2026/02/03共生场图灵测试 (SFTT)的设计Symbiotic Field Turing Test (SFTT) Design 本报告根据Google AI与Archer宏2...
-
 沃什、马斯克与钱宏 GDE 体系:把握宏观不确... 2026/02/02
沃什、马斯克与钱宏 GDE 体系:把握宏观不确... 2026/02/02沃什、马斯克与钱宏 GDE 体系:把握宏观不确定性的范式革命 Warsh, Musk, and Hong Qian's GDE System: A Paradigm ...
-
 从 GDP 到 GDE——如何切断“规模—外汇—互害”的... 2026/02/02
从 GDP 到 GDE——如何切断“规模—外汇—互害”的... 2026/02/02从 GDP 到 GDEFrom GDP to GDE——如何切断“规模—外汇—互害”的制度循环?How to Cut the Institutional Loop of “S...
共生思想理论前沿
THE THEORY
-

-

-

-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Symbiosism:Charles Thomas Taylor &Qian hong又一次量子缠绕...
查看详细说明
Speech
-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 ——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钱 宏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语从金音玉(Yǜ):金口玉言,一诺千金,性人诚恳、执信; &n...
-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点击播放 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访钱宏主持人:...
论全球共生机制的建构之四: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内部机制
摘 要: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问题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按照共生的生態学理论,国家权力结构犹如一个生態系统,中央和地方作为其中两个基本因子,形成共生互利、相互依赖、相互制衡,达到恊同发展的平衡状態。
关键字:共生;国家治理,治理机制
国家结构的本质问题是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它是国家建构的核心议题之一。按照共生的生態学理论,国家权力犹如一个生態系统,中央和地方作为其中两个基本因子,本应该是共生互利的关系,相互依赖,相互制衡,达到一种稳定的权力的生態平衡。然而,在几千年来的的中央集权思维并没有改变,中央政府一直把地方政府当做防范对象来看待,其骨子里认为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地方必然成为压迫和剥夺对象。在权力的生態圈内,中央就像一颗疯狂生长的大树,夺走了地方的养分精华。生態圈一旦失去平衡,也就充满了危机。
一、当今的中央政府是集权制度集大成者
从秦帝国建立起,中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然而,由于过去交通、信息等阻碍,中央集权的专制是有限的。比如在过去讲“皇权不下县”,显然是中央集权的触角无法深入到基层;再如,即使到中央集权最为隆盛的清朝乾隆年间,其中央财政收入不过4937万两白银,按照购买力计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财政供养能力仅为66万人,显然无法与今天的中央政府力量相对比。
到了现代社会,近一二百年出现的知识爆炸、技术爆炸,虽然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这也极大方便了中央集权制度的横行,政治学、管理学的出现大大改进了统治技术,现代交通、通讯、金融制度的出现使得中央随时可以干预地方,因此中央集权急剧膨胀。
中央政府对地方权力的侵占主要体现在:
第一,立法权。地方只有省和49个大城市有立法权,地方立法范围也仅限于城市管理、经济发展之类的;而美国联邦州都可以在征税、借款、设立法院的立法权,印度邦议会有47项立法权,包括刑法、经济与社会规划、人口、社会安全、教育、法律、等。立法权缺少反映的实质问题是地方无权决定自己的事务。
第二,财权。中央享有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车辆购置税等优质主税种,地方税种主要是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零星、分散的小税种。在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收入占50%以上,地方一般在45%上下。
第三,人事权。地方的领导不是自己选举产生,而是由中央任命。以往中央对地方的人事敢于只到省长一级,现在已经直接干预到副省级、地厅级。现任31个省区党委书记中有10个是中央直接空降,31个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有15个是中央空降。
第四,行政决策权。很多地方就可以自己决定的事项,决策权却在中央部委。2014年中央政府有1235项审批权,可谓事无巨细,甚至连全国4A景区建造一个厕所都要报住建部审批,一个中药材公司进口多少药材要商务部审批,所有机场、地铁、大型工业项目要报发改委审批,发改委“八大处”处长权力“一手遮全国”丝毫不夸张。
第五,土地及矿产资源所有权。中国的土地和矿产资源法律规定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形式所有权,这就使得当地方的土地、矿藏一旦经济价值凸显的时候,中央可以随时直接管理控制,中央通过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五矿、中有色等大型央企开发,实现经济利润,这也是近年来央企膨胀的一个制度因素。
二、国内诸多社会危机背后都是中央集权的问题
在这种中央集权制度下,好多国内问题看似是社会问题,其实背后是中央集权造成的问题在不同领域的反映。
地方债与土地财政问题。其实根源在于中央集权的“分税制”,地方政府在财政上无权,却要应付中央GDP的考虑,又要承担大量的事权(比如基层公务人员工资、教育、社保、基建经费等),地方要用45%的财政收入,承担75%的财政支出,40%的县有财政赤字。因此,地方不得不靠卖地或发行地方债来维持财政收入,目前中国地方债在15万亿到20万亿之间,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度不稳定因素;而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每年财政收入一半以上要靠卖地来维持,这又是导致房价高涨不下的诱因。
首都的大城市病问题。在中央集权的怪圈下,一方面,中央政府只能是规模越来越大,为了实现对全国的绝对控制,中央必须设立越来越多的部门。比如以往管理金融的只有中国人民银行,现在又有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以及各种办公室、领导小组、官办恊会,北京的政府机构越来越膨胀;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有绝对权力,权力机构就成了这个社会的中心,个人或机构为了更好发展往往不自觉的去依靠它,这样北京就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并且它这种吸附效应会越来越强,不会因为有雾霾、交通阻塞、高房价抵挡外地人进京的步伐。
所以,北京出现大城市病是必然的,并且在短期内病的越来越重。即使现在推出京津冀一体化,如果不解决北京行政资源过度集中的局面,北京的其他经济、教育、金融资源是不会转移出去的,一体化只能是空想。
地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各个地方都有机会发挥区位、资源、人力、交通等潜能,比如在清末民国,即使在内陆的山西乡下也诞生了太谷、平遥这样的金融中心,武汉也一度超越上海成为中国最大城市。然而,在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控制资源的分配,中央决定资源的价值,中央重视谁谁就发达。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有限资源投入在东北、上海、北京少数几个地方,东北的工业总产值曾经高达全国70%。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财政投放和政策倾斜又放在东南沿海。而中西部长期的资源禀赋被压抑,虽然近年重视中西部发展,但是积重难返,任重道远。2013年,各省人均GDP最高者15760美元,最低者仅3690美元。若以城市为单位,最高者36400美元,最低者仅1315美元,这在一个民主的过度是不可能出现的。
边疆分裂问题。中国的新疆和西藏问题,本质不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表现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种族对立,然后引起民族对立乃至分裂倾向。然而,在中国,汉族和藏族、维吾尔族其实并不存在这些问题。在宗教上,汉族向来重视实用,对于任何宗教都是拿来主义,并不排斥任何宗教,西方的宗教冲突,并没有在中国发生过,西藏的汉族、新疆的汉族和藏传佛教或伊斯兰教相安无事。就个体来讲,在边疆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总体是和谐的,在南疆村里有汉人也有维族,大家相处都很好,在内蒙汉蒙关系更融洽。所以,新疆、西藏问题绝对不是民族矛盾造成的,少数民族仇恨的不是汉族人,仇视的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
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现在香港占中和政改僵局,根本上还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权的较量,而不是官方媒体宣传的境外势力支持的颠覆活动,搞颜色革命。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在香港高层人事任命上有绝对控制权,中央在香港还有两万名精锐部队,中资企业也渐渐控制了香港的经济命脉。但是,中央集权的政府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它对于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实现绝对控制,所以在香港还要搞“国安条例”、搞“国民教育”、控制香港选举。中央的这些做法,显然是危害了香港的自治权,触犯了他们的地方意识,才出现这个问题。如果中央没有和谐共生的思维,肯定香港还会闹下去,香港民众会越来越激进,香港社会也会撕裂,这对香港和中央政府都不是好事。
现在台湾不敢谈统一,以及2014年年初的“太陽花”学运,根源还是在于对一个专制中央集权政府的惧怕,因为你无法跟他共生,终究将要被吃掉。二战和冷战造成的政治分裂都已经解决了,东西德统一了,南北也门也统一了,唯独剩下台湾和大陆不知还要分裂多久。国民党老是讲,和大陆统一的前提条件是大陆必须实现民主化,这看似是一个意识形態的问题,实则是能否共生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才能会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中央才会尊重地方,台湾人民的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才能得到保全。
三、中央集权实质增加政权的不稳定性
中央集权主义者认为中央政府越大,国家就会越稳定,而事实是中央政府越强大,国家的风险越大,其政权稳定性越差。究其原因,出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央集权使得社会矛盾同质化,由于全国制度是高度统一的,社会矛盾也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地方的社会问题都会引发全国的危机。比如,全国各地的征地拆迁矛盾都很严重,一个地方因为拆迁出了骚乱,其他地方人民也会有类似心理,也可能引发相似事件。
第二,中央集权使得任何社会矛盾最终转化为政治问题,任何社会问题都可能引发政治危机。
第三,中央集权使得中央成为任何社会问题的怨气所在,任何社会问题都要中央政府来解决。比如现在基层老百姓无论大小问题都来国家信访局上访,国家信访局一年要处理信访信件、访民900多万次,是全国最忙的一个机构。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18世纪法国那样,“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
所以,中央集权看似强大,其实这种稳定性很脆弱,所以只能靠高压“维稳”来维持。中央在把权力集中过来的同时,其责任和风险也随之而来。
四、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实现中央与地方共生
所以,中国仍然是一个缺乏国家与地方共生意识的“传统帝国”,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建立在一个强大中央集权的基础上。然而,这个体制不能支撑国家的长久稳定与繁荣。要建设一个符合共生原则的国家结构,要考虑以下问题:
第一,中央和地方行省方面,应该通过宪法和一系列法律科学分权。重点明确中央在立法、财政、人事、行政决策、经济上的界限在哪里。在政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太多国外经验可以参考,这应该不是什么难题。
第二,中央与少数民族地区方面,中央除了要赋予少数民族地区地方一般拥有的公共领域的地方自治权外,还应该考虑给予一个民族作为族群实体的特性,给予相应的民族自治权。
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管得越多,中央权力越大未必是好事,这已经在几千年来历史上反复证明了。无论是两汉还是唐宋,每当中央在胡羌地区推广中央集权都会引发叛乱。明清时期自治权较大的蒙藏地区,也远比改土归流的川滇地区稳定。
第三,中央与港澳地区(以及以后的台湾)方面,要有充分的制度包容。港澳台地区的制度都已经有百年以上的渊源了,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和制度优势,从实施现状上来说,效果是远远优于内地(大陆)体制的,中国政府应该尊重这些地区先行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遵照港澳台本地制度发展的规律,而不是阻挠其发展,甚至强行与内地制度靠近。中国政府更应该看重港澳台制度对内地(大陆)的反哺价值,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内地经济、住房、医疗、教育等制度大量吸收了香港制度;从未来看,港澳台制度也是中国未来政治改革的最直接参考样本。
第四,国家结构的共生建构不是一个孤立课题,应该与民主及法治结合起来。只有依靠民主,才能体现地方治权是本地人民所赋,而不是中央随意赐予的。也只有民主才能保障地方治权被合理利用,专制体制框架的地方自治,不过是由“皇帝集权”变成“诸侯集权”,犹如北洋时期的中国,平白增添几十个土皇帝而已,地方自治极容易被政客当做要挟中央的挡箭牌。
同时,也只有法治体系才能公正解决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的模糊地带和冲突,形成中央与地方的良性互动。比如,香港基本法对香港自治权有很多模糊地带,但是中央通过全国人大释法这套法治程序,都比较妥善解决了,比如居港权、外交权等问题。而中央与内地地方权力还多是通过领导批示、行政命令等方式恊调,所以永远扯皮不清。
现代社会,民权、自治、民族等思想日益高涨,这是大国转型中不可回避的门槛,20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苏联)都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而在历史潮流中瓦解掉。中央集权带来的弊病对中国的考验也越来越严重,建立一个最大限度包容的共生制度,从现在来看是一个化解矛盾最有效的方式。
王明远,全球共生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本文为2014年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嘉义)的主题论文。
上一篇: 共生哲学——科学精神与中国之道的共融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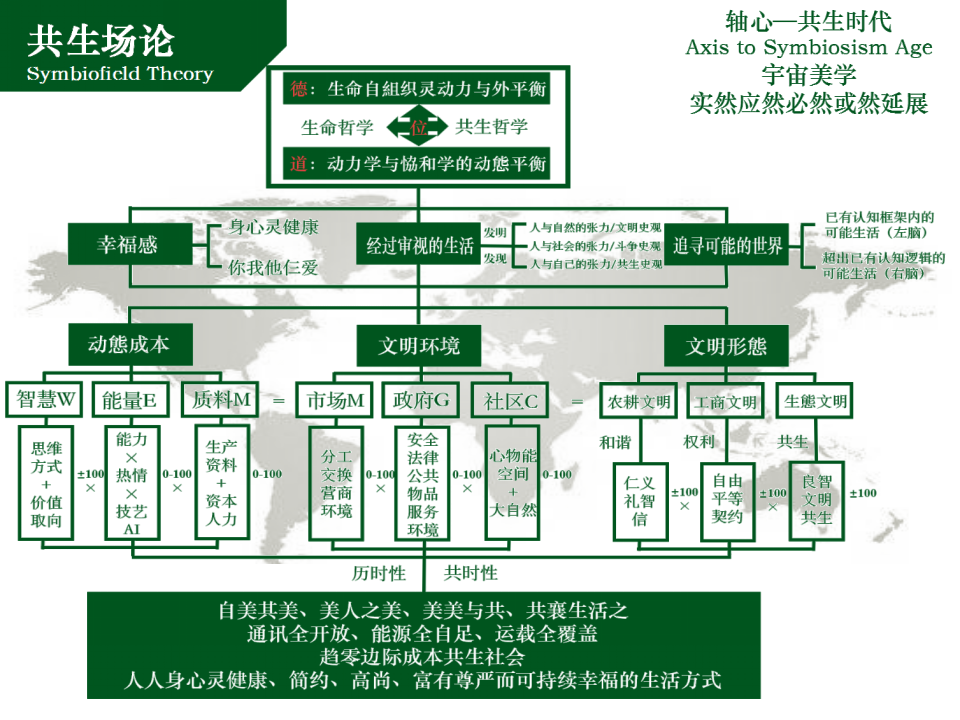





您好!请登录
已有0评论
购物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