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Articles
-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2026/02/24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2026/02/24【共生经济学·前言】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The Cognitive Bias and Fragmentation of Economics as...
-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2026/02/22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2026/02/22《共生经济学》自序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How Should We Face the “Ultimate Free Lunch”? 一、从宇...
-
 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2026/02/17
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2026/02/17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Modern National Normalization under the Global Symbiotic Paradigm ...
-
 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2026/02/16
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2026/02/16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Chinese Reproductive Officialdom: Why Regime Change Has Not...
共生思想理论前沿
THE THEORY
-

-

-

-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Symbiosism:Charles Thomas Taylor &Qian hong又一次量子缠绕...
查看详细说明
Speech
-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 ——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钱 宏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语从金音玉(Yǜ):金口玉言,一诺千金,性人诚恳、执信; &n...
-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点击播放 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访钱宏主持人:...
钱 宏:以共生的名义:重塑“私有财产”与有公信力的公权力
发布时间:2019/07/28 政治 浏览次数:966
从“三个代表”到“新三大法宝”
一、中西社会差异:官民矛盾与阶级斗争
二、“三个代表”:无限政府与有限政府
三、以共生的名义:重塑私有财产与公权力
四、社会机体修复:积极改良与恐惧革命/煽动革命
五、共生权范式:新三大法宝与《中国法典》
一、中西社会差异:官民矛盾与阶级斗争
张雪忠以“白馬非马”辨“中宪非憲”很有意思!
但在中国,以“立宪主体”“主权与治权是否分离?”以及“主权能否限制治权?”为鑒憲法真、伪的標準,依旧不能改變“官(精英)本位”制度-文化-人性背景下,权力精英们“選擇性執法”,而全体草根们被“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政治行径所愚弄!
比如,中国《八二宪法》第9、10、15条中规定的“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等对官僚集团(类神甫集团)有利的部分,他们会不折不扣变本加厉地执行到恶心的地步,而对《八二宪法》第2、33、35、41条规定公民权利的部分,他们有的是办法搞到“成为实际上的不可能”而且似乎还不“违宪”(中国根本没有独立的宪法法院及独立司法)。
中國大陸的根本问題,是“官民矛盾”,这与西方的“階級矛盾”是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
“官民结构”与“阶级结构”的区别在于,官是有组织的(借国家之名“垄断全部政治权力”),民是原子的一盘散沙(所谓“老百姓”),且被分成“自己人与异己分子”“人民内部与人民外部”及“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三六九等”的身份加以区别,只有在造反时才会形成组织力量,但完成改朝易姓政权更迭新的官僚集团成形之后,部分民转入官的行列外,民在政治意义上的一切自组织包括所谓的“农会”或“工会”都必须解体。所以,即使在大革命时期勉强可以做“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也完全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实际上,并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因为阶级,并不简单是个经济状况的表述,阶级通常都有作为阶级的社会自组织性与外平衡力,而且,不同的阶级,具有相应的“阶级意识”。
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社会的阶级,都是有组织的,即无论什么阶级——从皇族或教会僧侣、世俗贵族、第三等级或市民资产者、平民(农民、工人)——都可以形成各自机体的自组织力量,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价值观,这些阶级的自组织力量分化组合,上下流动,相互制衡,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
这一中西差异区别,非同小可!我曾在“《改革内参》高层报告首次特约专家、研究员座谈会”(2011)上,就“全生態社会建设”(2007)这一当今时代主题,提出中国当下面临的关键问题,集中反映在两个关键词上:一个是“官生”,一个是“民生”。由此,我给出一个公式:
共生﹦官生×民生×(5大笃行步骤)
民生,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那个民生主义,按照孙中山自己的解释,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后来,或许是照搬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缘故,民生、民生主义就在我们的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中消失了。即使近十年来常常成为“两会”热点,但离民生主义依旧相去甚远。
官生,是本人生造的一个词。只要了解改革开放历史的人都知道,四十多年前,中央财政窘迫,支付不了各级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官员的工资,特别是一批批进入基层组织和政府的转业干部,“官生”出现问题。对一个中国政权来说,历来民不聊生事小,官不聊生事大。何况官生也直接影响民生,“官生”问题逼上梁山,所以不得不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力与共识,就是为了解决“官生”问题。但是,四十年之后,大家渐渐发现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年年急剧增长,“官生”已被“官富”(有网友造了个字:[i])所取代,“官不聊生”的问题,早已变成“官多为患”(张全景)“官满为患”(刘锡荣)的问题,而“民生”问题则越来越严峻,甚至险恶。有学者甚至提出,“民生”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不改革,将是死路一条。可问题是,改革可以解决官不聊生的问题,改革能不能解决民不聊生的问题?历史上,解决民不聊生的问题往往是革命。所以,说当下中国是改革与革命在赛跑,同时由于“官”又丧失了改革的动力,而社会由“仇富”转向“仇官”的激进化,也使改革越来越丧失共识、丧失空间。以至于许多人担心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特别是宋代王安石改革(冗官而敛财)的悲剧在当代重演(参看《中国:共生崛起》P135-143,知识界产权出版社,2012.5)。
二、“三个代表”:无限政府与有限政府
那么宪法,在西方,是作为平衡不同阶级组织力量关系实现正常社会生活的根本大法。为了这种法理意义上的再平衡,宪法将所有阶级关系,高度抽象为“人民”(主权)与“政府”(治权)关系,并将国家“主权在民”定为天经地义,这就是美国宪法中体现的“自然正义”,然后才有政府形成的“约定正义”。
特别是在美国,这个与人民(主权)相对的“政府与行政当局”(治权),是严格区分的两个概念。使用“Government”表达的主要含义,是“政府”、“政体”,也有“行政管理”和“管理机构”的意思;而使用“Administration”表达的主要含义,是“管理”,“行政机构”或“行政当局”。
在中国,缺乏约定正义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机制条件下,特别是在“成王败寇”和“打天下,坐江山”的中国政治语境里,可以“选择性执(宪)法”的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都能够以政府(Government)代表自居,以至于当权者(Administration)能够以“三个代表”自居,以致完全消解或掏空了“人民主权”自然正义的哲学支撑。“三个代表”的意思,就是当权者(Administration):
第一,包揽思技创新——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第一个代表,是虚妄。当权者能代表网络化、人工智能、电子通讯,能回答并解决“李约瑟-钱学森之问”吗?根本不可能做到,如果强行设置政治经济产业规划机制(言必己出、行必己令、利必己分),介入生产力创新管理,结果只会对内抹杀个人和企业创新(或贪天之功为己有),对外隐性或显性强制窃取或转让,制造社会摩擦与国际冲突,为中国国民和企业有个性地融入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设置人为的国别合规障碍。
第二,包揽价值标准——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第二个代表,是自大。也根本做不到,没有任何政治组织可以设定一个国家先进文化的价值目标,先进文化不可能来自当权者的“顶层设计”(与“底层驱动”相对),而一定是基于中国国民与社会自组织内生性灵动力与外平衡力,如果第二个代表与利益分配上的第三个代表结合,其结果只会把中国人带到沟里去,造成伦理道德上的混乱,例如1990年代确立的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控市场经济”,公然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结果就是我们今天随处可见可感的官民、官官、民民、中外之间,竞相坑蒙拐骗的机会主义横行;
第三,包揽资源分配——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第三个代表,是事实。能做得到,亘古以来只有中国当权者可以借成文宪法(“八二宪法”第9、10、15条)之名“选择性执法”,公然在自然资源、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分配上,无所不用其极堂而皇之地“与民争利”,威逼利诱广大人民在根本利益上依附于当权者小圈子转,且不说各种强拆和司法腐败遍布国中,最最荒唐的是底层人民连“摆地摊”自谋生计的权利和尊严,都时时受到当权者的威胁(湖南打死瓜农、北京驱赶DDRK,只是“偶尔露峥嵘”的冰山一角)。也正是这第三个代表,成为当代中国一切思想(“以公兑私”天然正确)、政治(“公权私用”方便法门)和经济(“以公肥私”无孔不入)问题的总祸根——造成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矮化自己。
我无意于批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其当权者的现实问题,只是在概念上澄清其名与其实——实行“包揽思技创新、包揽价值标准、包揽资源分配”三包的无限责任权力政府,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土地自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承受极限。而且,无限政府,实际上就是无视本国公民生命自组织力和社会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对自己国民的自然法权缺乏起码的尊重!
我在《关于政府、国家、教宗、邻居与战争的思考》(刊《经济要参》2015年第23期)谈到:即使是由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几大部门组成的GOVERNMENT(政府),也不能完全代表一个稳定区域的国家,因为政府总是有时限、有权限(责任)的人的组织集团,而国家是个文化综合体(共生体),因而国家是承载着这个文化综合体(共生体)的无时限、无权限(责任)的人民、公民、国民及其各有限责任社会组织(含政府)构成。
所以,哪怕在中国的王朝时期,朝廷内阁、政府也是可以不断换届的,何况“改朝换代”的事也经常发生,但是,国家并不会因为哪个朝廷、政府的更替而灭亡了,除非天灾人祸或强敌入侵把这个区域的人民、公民、国民都赶尽杀绝,其文化共生体也随之消失了。
因此,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中,将一个朝廷、政府规定为无时限且拥有无限权力,而承载一个区域文化综合体(共生体)的人民、公民、国民的生产、生活、生態,反倒是有时限、有权限的,结果一定会产生马克思终身宣战的对象——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法定特权!而这样的朝廷、政府、官僚集团或神甫集团,一定会长成霍布斯描述的有着无限吞噬能力的大怪物——利维坦,亦即成为国体、政体、经济体内的“恶性肿瘤”。
这样一来,无限权力也就走向反面,即内外丧失“公信力”。有一个最朴素的常情、常理、常识:如果一个国家的当权者只顾自己揽权占尽便宜,不能尊重自己国民生产生活的最基本权利,言必己出、行必己令、利必己分,如何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友情与尊重?
既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也要搞现代政治文明,搞“政党政治”(相对“强人政治”),无论是搞一党(事实上多派)专政,还是搞多党轮流执政,都应当回到人类最基本的政治生活准则——即基于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哲学的宪法秩序。否则,无论“三包”无限政府(Administration)及其当权者,取得怎样的“经济成就”,都不是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可能用直觉判断(常情、常理、常识与情理、道理、法理)的正常国度!
任何公权力,一旦丧失公信力,就必然遭遇“商鞅-桑弘羊-塔西陀陷阱”。公权力丧失公信力的根源,就是直接违背了这样的常识、常情和常理:很简单,当权者(Administration)为了对国民“私有财产”提供安全保护和对国民交集提供公共物品,可以垄断暴力,垄断税收,但不能垄断国民赖以生产、生活、创新、交税、换取安全保证的资源,尤其是信息资源、国土资源,正所谓“身土不二”——国民者国土也!
三、以共生的名义:重塑私有财产与公权力
如果把这种非正常状態,叫做“中国模式”,那么,中国模式的要害,就是“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内在矛盾与“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的政治死结。
怎么办?历史上有两种办法,一是强调“为了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这是菲尔麦以“君权神授和宗法”的名义,写成的《论父权制或国王的政治权力》的办法,其要害是让“多数人”逆来顺受,所以也是汉儒“天人感应”的伦常规范。
菲尔麦和汉儒的办法,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激发出另一种相反办法,即革命或造反。革命或造反,主张“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但也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结果又往往只是“改朝易姓”轮换一批流氓坐赃,这就是中国宗法专制社会两千年治乱循环的政治哲学维谷。
显然,过去100多年、70年、40年来,中国分别以“革命的名义”、“继续革命的名义”、“渐进(跛足)改革的名义”,都没有解开这个“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内在矛盾与“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的死结,而如今中国无论是“官”是“民”,无不再次陷入“恐惧革命或煽动革命”的政治维谷之中。那么,当代中国人就注定要自创新的哲学及其意识形态——以共生的名义——加以解决!
共生(Symbiosism),是活体间的一般存在方式、生活方式、生態方式。从宇宙天体到地球众生灵,从个体、群体、国体、政体、经济,到人类社会,都是活体,生命之源,共生一体;而任何活体,尤其是个人,都具有生命自组织内生性活力与外平衡力,懂得一视为仨,和实生物的价值;因而必须发挥“道不同,亦相与谋”的智慧,尊重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人(live and let live),存同尊异,间道共生。
所以,共生哲学,不对自然、自由、自在的生灵进行是非、真假、善恶、好坏、君小、敌友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预置,“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果有敌人,那就是自己(智慧不够、格局不大又奢侈贪婪);共生哲学,不舍弃任何人,无论是你、是我、是他(她它祂)、无论是自己人、是异己者,无论是官、是民、是少长、是男女、是动物、是微生物(地球生態受“共生菌”调节);因而,只有以共生为人类伦理价值底线,并“以共生的名义”,在中国大地上重新确立“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才能在“三常”(常情、常理、常识)、“三理”(情理、道理、法理)的直觉判断与感受上,生成“官知进退,民谙厚德,天下相安”之世风,自觉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走出秦汉之后两千年治乱循环的梦魇。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洛克《政府论》中面对《论父权制或国王的政治权力》问题的因应之道——从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切入,重新梳理私有财产与政治社会公权力的关系。
以共生哲学观之,我们注意到,作为英国光荣革命的见证者、参与者、辩护人和一个清教徒,约翰·洛克(John Locke)所谓的财产(拉丁文proprius),是以个人所有物为基础。所谓私有财产,指称的是:一个人经由自组织(劳动)所拥有的东西——首先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因此,每个人也必然有权利在自然足够慷慨赋予的资源上混合他自己的劳动(自组织)所得的产品。所以,洛克所谓的“私有财产”包括了人人生而拥有“生命(平等)、自由(信仰)和财产”的权利。这即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讲的自然正义!
为了对拥有“个人所有物”的权利,提供更好的保护,同时,为了获取与社会共同体其他人交换劳动(外平衡)才能实现的增量利益,以便各尽所能,共襄生活生长(Grow by Symbiosism),人们创立了政治社会,形成了公权力(相对于私有财产)。所谓公权力,就是对重大利益进行权威分配调节的力量。这个公权力“政治社会”,在英国光荣革命后开启的世界近代进程中,叫“公民社会”,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叫“江山社稷”。但不管叫什么,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亚里士多德讲的约定正义性质!
在这个意义上,洛克说出了一句警世名言:“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政治社会”,或“江山社稷”,或“公民社会”,无论是军事集团打出来的,还是王位继承来的,抑或民主竞选来的,都必须具有保护个人所有物权利,及促进每个人正常交换劳动获取增量利益共襄生长的“约定正义”性质——这意味着公权力由信托而来(“权为民所赋”)——这既是公权力的法理基础,也是公权力的公信力基础。
所以,洛克明确指出:政府必须根据正式颁布过的、长期有效的法律来治理,而不能依靠临时的专断命令(批示、红头文件)来进行治理。法律一经制定,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必须平等地服从,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逃避法律的约束与制裁。
迄今为止,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度,无论是阶级社会,还是官民社会,对于公权力与公信力最有效最公平的政治保障机制,就是宪政秩序。
我想说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要形成“私有财产+公权力(政治社会)”,无论是“私有财产+江山社稷”,还是“私有财产+公民社会”,都具有共生社会机体的基本形態(Basic Forms of Symbiotic Social Organisms)属性。
四、修复社会机体:改良与恐惧革命/煽动革命
但是,如果以为只要有了“私有财产+政治社会”这一基本形態,就一切OK了,那显然是政治上的幼稚。
即使是宪政秩序稳固共生社会,也依旧会遇到洛克著述《政府论》之后的人类,所遇到的“两极分化”(基尼系数0.4以上、强势弱势阶层对立、帕累托最优成为不可能)问题,亦即“多数人或少数人”,以某种“以公兑私”“假公济私”的主义、宗教、圣域或区域特色,为机巧借口,偏离“约定正义”,而不能不对“政治社会”进行积极改良,抑或陷入恐惧革命或煽动革命的周期性政治维谷之中。
积极改良(保守而又创新),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因而要理想、要科学、要斗争(批判、扬弃),不要理想主义、科学主义和斗争主义,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谁都别想一劳永逸而偷懒,把自己的命运悉数交给任何共同体组织!
我们生为人类,别无选择,必须永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共襄生长(Grow by Symbiosism)的精神体能与生命自组织灵动力!
当一个人,或一部分人,或某特殊共同体,通常是“君臣共治”或军事集团转化来文官集团及其成员,或“权力、资本、知识精英联盟”(类宗教改革前的“僧侣集团”),通过创租、抽租、寻租或干脆赤裸裸的强夺强占,拿走超过他和他们,能使用到的自然资源(财富)数量。而且,这种情况在权力操纵和资本垄断趋同的条件下,会造成大量糟蹋自然资源和奢侈浪费,同时,政治(恊商)设计的“法治和分权制衡”,以及洛克提出的两个取得财产的但书(proviso,法律规定的限制、例外、补充、相反关系和充要条件,如“同样多和同样好”的存量条件和避免“浪费糟蹋”的限制条件),对这个人、这一部分人、这个共同体(利益集团、神甫集团、强势阶层)都不能发挥制约作用——一句话,当一个人、“一部分人”或利益集团,混淆“孰公孰私”关系,唐而皇之地“以公兑私”“假公济私”,而无视“财产私有”的自然正义,又偏离“权力公有”的约定正义时,又怎么办?
是的,洛克说了,中外历史事实也证实,革命、继续革命、改革的合法性。既然国家权力是受人民委托来实现某种目的的,那它就必然要受那个目的的限制,当这一目的显然被忽略或遭受打击时,委托必然被取消,权力又回到当初授权的人民手中,人们又可以重新把它授予最能保卫自己安全的人。因此,政治社会始终保留着一种最高权力,以保卫自己不受任何团体、即使是他们的立法者的攻击和谋算。当政府已经开始祸害人民,统治者的恶意已昭然若揭,或他们的企图已为大部分人民所发觉时,人民就将被迫揭竿而起,推翻他们的统治了。以共生哲学观之,这本是一个正常社会机体,通过社会自组织力进行机体修复的行为。
但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可能总是革命、继续革命,也不能总是改革(含“改恶”与“改良”)吧?其实,科斯发现,一个正常的社会,重要的不是贫富不均本身,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贫富不均。如果贫富不均是公平竞争且符合帕累托法则(The 80/20 Rule )的结果,人们会广泛接受;在众人眼里,成功者是他们的英雄和榜样。只有当贫富不均是贪污腐败的结果时,它才会煽动嫉富、仇富和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和敌意。
何况,无论是革命,特别是“社会大革命”,还是继续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抑或改革,特别是官家“敛财式改革”(改恶),结果证明,并没有达成恢复或修复“私有财产+政治社会”机体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的效果。而更多地是,要么造成社会机体的大面积破坏,要么长出新的利益集团恶性肿瘤,对整个系统机体的活性构成颠覆性威胁,重复历史上的“制度-文化-人性”恶性治乱循环。正如圣西门所言大革命“这一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只是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 “现有政治体系的三个主要弊端,即专横无端、腐败无能和玩弄权术”。
由此不难发现,陷入恐惧革命或煽动革命政治维谷,首先都是对社会机体(人体、群体、国体、政体、经济体)活性机制认识不足的表征。而迄今为止,从修复社会机体重新获得自组织活力与外平衡力上看,最可取也最成功的方式,是具有积极改良(保守而又创新)属性的“光荣革命”。
五、共生权范式:新三大法宝与《中国法典》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生论者针对中国特色提出了“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的著名论断。
今天,我们不难发现,信奉“因信称义”,从而简单、实在、人人平等、彼此造就、相互坚固地生活的价值观,经过荷兰、英国、美国清教徒们在亲历亲为“私有财产+政治社会”时,建立起了一整套“制度-文化-人性”良性循环机制,成就了无需不断革命或改革而能创新不止、生生不息的荷兰王国、英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这并不是说荷、英、美体制终结了人类政治社会体制的历史,而仅仅是说荷、英、美的人们建立了一种能够对政治社会机体进行自我修复,积极改良,让社会各阶层和解共生的机制。比如1688年光荣革命后近500年来,英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今引领世界政治文明潮流,而没有发生过一次内部战争(参看《钱宏在DC:和解共生与中国再造——兼议改良中国政治生態环境的十六个切入点》,《中国:共生崛起》P234-248)。美国也同样如此,尽管爆发了一场南北战争,但战后胜利的北方与南方很快实现了“和解共生”,又以一部《谢尔曼反垄断法》(1890)、一场进步主义运动(1912)、一部《证券交易法》(1934),解决了“劳资矛盾”和“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问题,实现了“资本社会化”,而且,二战后改写了人类战争以“屠城”和“割地赔款”方式奖励胜利者的历史。
这是今天处于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的人类,需要真正下功夫了解和戮力笃行的活生生的“经验”(相对于死的模式)!前面已经说过,对于人类组成的政治社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谁都别想一劳永逸而偷懒”,所以,当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时,我写了《共生政体:中美模式各自大有改进空间——写于福山<身份>将问世之际》(2018)和《重建世界秩序: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刊《经济要参》2018年第49、50期;《战略与管理》,2019年第一期)。
共生学人还发现,提出并践行社会主义思想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马克思们的优长,是和清教徒一样,提出了以“每个人的自由为一切人的自由的前提”和“每个人的平等为一切人的平等为条件”为政治社会出发点。但可惜,其达成这一目标的方式,即以“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或“资本主义”,在其后世革命、继续革命和渐进改革的效果,却与其出发点完全背道而驰,结果依旧不能从“多数人与少数人”的政治维谷中走出来。究其原因,是背离了“私有财产+政治社会”的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同时,未能明确认识到,确保每个人生命自组织内生性活力与外平衡力的整体发挥,才是“私有财产+政治社会”的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的价值落脚点。
于是,共生哲学强调,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的任何人,都享有相应的共生权,即相应的人权、事权、物权。基于宪政秩序的共生权解套“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死结的现实力量定位,这里再次强调“新三大法宝”:
第一大法宝:人民中心,重建社会,针对“社会主义”、“共和国”如何名副其实的问题。
第二大法宝:瘦身去瘤,培元固本,针对“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问题。
第三大法宝:生態统领,共生为魂,针对社会交易成本、边际效益成本与国民幸福指数、尊严感呈反比关系问题。
新三大法宝,第一次发表在《经济要参》2015年第50期上。三大法宝直接价值指向是:中国社会主义共和国国体的性质,及其“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决定了中国政体及政权的价值承诺、制度定位、政策导向分别是:
“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承诺,这是国家公权力公信力的文化基础。
“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承诺,决定了国家的民本位(相对官本位)或人民中心的制度定位。
第三,民本位的制度定位,决定了国家权力-财富三大政策导向:一是权力的制衡战略(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媒体、咨政七权分置);二是财富创造战略(以能耗、能效转换为基准的GDE评价体系);三是财富分配战略(以共生权平衡官、民人权、事权、物权)。
共生权定位下的依法治国,是在信仰和哲学上确立三大法理原则:一是对国民而言,做你自己愿意和同意做的事情;二是对政府和集团而言,不要做侵犯他人或其财产的事情;三是是对所有官民而言,一切言行始终贯通“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而不要“自己邪恶,也让别人邪恶”(evil and let evil)底线原则。从而明确社会各阶层的权益边界与流动机制,因此,需要以基于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的宪法及宪法法院为法理实践基础,确立一部划时代的《中国法典》。这部划时代的《中国法典》,由《宪法》和这样三部法典构建:
第一,以《反操(控)纵法》、《行政许可法》为基础,停止《八二宪法》第9、10、15条,制定规范公仆、管家行为的《官法典》;
第二,以《八二宪法》第2、33、35、41条为前提条件,并新制订《国民事权法》为基础,确立民事行为的《民法典》;
第三,以《刑事诉讼法》,并新制订《赎买特赦法》为基础,惩治官、民越位、越界行为的《刑法典》。
共生权法理定位下“私有财产+政治社会公权力”的价值目标指向,就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过程中,实现“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陽子哥2019年7月21日于童心公寓
——————————————
[i],从官从田,取富字的声母和官字的韵母,音藩fān,即藩篱的“藩”同音,且部分同义,意为官阶,官本位,官商勾兑,升官发财,官占田地而富,即“富官”、“富官政策”与“富民政策”相对,引申义为与民争利的中国特色之城市“市长型市场经济”,具体含义为GDP增长率政绩参量主导的“土地财政”等。
附录网传张雪忠老师的贴子:
为什么说在中国“宪法”是最具“奥威尔式”话术色彩的用语?
美国联邦宪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成文宪法(不考虑克伦威尔的《政府协约》和美国各州宪法的话)。随着这部宪法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个人自由的作用,不少国家也开始效仿美国的做法,基于类似的原则制定本国的宪法。
在这一过程中,“宪法”逐渐成为一个极富正面意味的用语,连那些完全不认同现代政治原则的政权(这些原则与现代宪法概念是不可分离的),也开始炮制被称为“宪法”的文件。首先这样做的是一些专制君主国(比如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君主以最高主权者的身份将一部体现君主意志的“宪法”赐予国民。后来,一些由单个政党垄断全部政治权力的国家也这样做,执政党将一部体现本党意志的“宪法”加于国民。
这些东西在专业的宪法学上被称为“伪宪法”,因为它们只是将与现代宪法格格不入的政治制度,用“宪法”这一用语掩饰一下而已。这种扭曲词义、滥用语词以混淆概念的做法,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奥威尔式”的话术。
要知道,现代宪法之所以可以约束政府权力,或者说之所以是有必要的,是在于全体国民是主权者,但却不亲自进行国家的日常治理,因此就制定一部宪法来规定政府权力如何产生,以及它的范围和行使方式等。也就是说,代议制所体现的主权与治权的分离,使得现代宪法成为必要和可能。全体国民的主权,主要是制定宪法的权力。宪法一经制定,作为主权者的全体国民就隐身了,人们都以公民的身份在宪法之下行使各种权利(全体国民若再次现身制定新宪,那就意味着发生了政治革命)。美国宪法开头的“我们人民”这一表述,其政治哲学与宪法政治学的含义即在于此。
而在专制君主国或一党执政的国家,君主或某个政党既是制定“宪法”的主权者,又是日常的国家治理者,因此主权和治权不是分离的,而是由同一个政治主体享有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在正常意义上使用“宪法”这个词。试想一下:如果宪法内容是国家治理者自己来决定的,它怎么可能起到约束国家治理者的作用?而不能约束国家治理者的东西又怎么能说是宪法?
基于以上考虑,每当看到有法学学者呼吁执政者落实宪法、保障公民权利时,我就像看到不懂事的小孩指着和尚手中的木鱼说:“师傅,我肚子饿了,能不能把你手里的鱼煮给我吃?”
不懂事的小孩不知道木鱼不是鱼是可以原谅的,专业的法学学者不知道现行“宪法”不是宪法却是不可原谅的。(张雪忠)
钱 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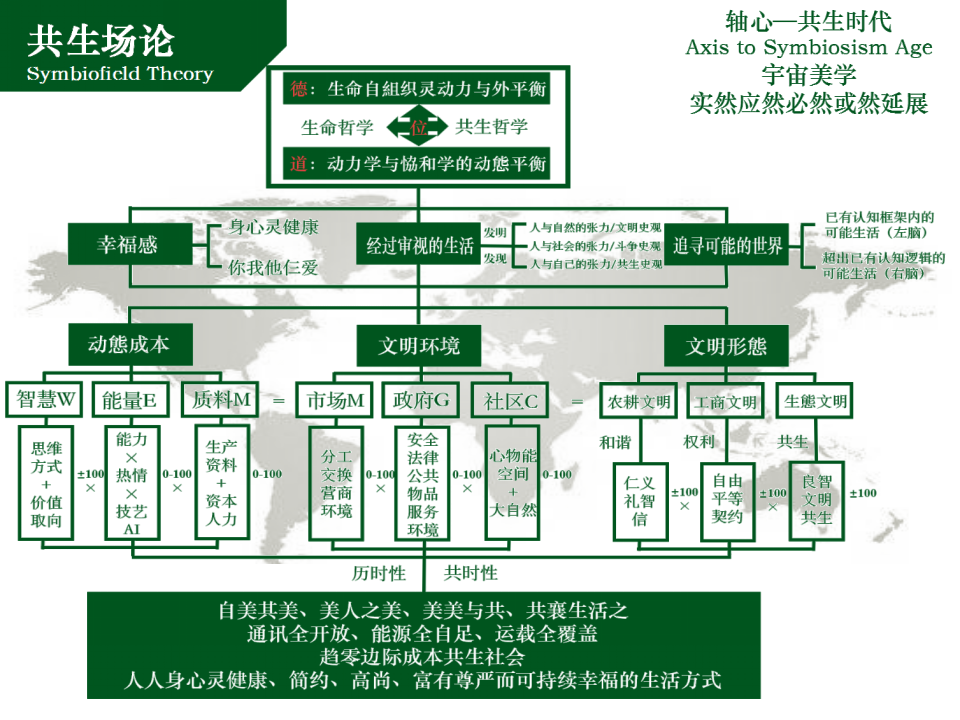





您好!请登录
已有0评论
购物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