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Articles
-
 AI三大瓶颈及其10个“傻白”和5个“傻精” 2026/02/04
AI三大瓶颈及其10个“傻白”和5个“傻精” 2026/02/04AI三大瓶颈及其10个“傻白”和5个“傻精”The Three Major Bottlenecks of AI and Its “10 Naïve Blind Spots” and “5 Cunnin...
-
 共生场图灵测试 (SFTT)的设计 2026/02/03
共生场图灵测试 (SFTT)的设计 2026/02/03共生场图灵测试 (SFTT)的设计Symbiotic Field Turing Test (SFTT) Design 本报告根据Google AI与Archer宏2...
-
 沃什、马斯克与钱宏 GDE 体系:把握宏观不确... 2026/02/02
沃什、马斯克与钱宏 GDE 体系:把握宏观不确... 2026/02/02沃什、马斯克与钱宏 GDE 体系:把握宏观不确定性的范式革命 Warsh, Musk, and Hong Qian's GDE System: A Paradigm ...
-
 从 GDP 到 GDE——如何切断“规模—外汇—互害”的... 2026/02/02
从 GDP 到 GDE——如何切断“规模—外汇—互害”的... 2026/02/02从 GDP 到 GDEFrom GDP to GDE——如何切断“规模—外汇—互害”的制度循环?How to Cut the Institutional Loop of “S...
共生思想理论前沿
THE THEORY
-

-

-

-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Symbiosism:Charles Thomas Taylor &Qian hong又一次量子缠绕...
查看详细说明
Speech
-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 ——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钱 宏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语从金音玉(Yǜ):金口玉言,一诺千金,性人诚恳、执信; &n...
-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点击播放 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访钱宏主持人:...
重建世界秩序: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下)
重建世界秩序:
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的著作权不属于美国人
我有朋友说,美国人说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说美国错了,中国是社会主义。美国是错了,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美国人的发明,没有必要反驳美国人中国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德国的李斯特,但为列宁首倡,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国家政权对企业的控制,“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二是指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监督和调节,“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由于情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列宁在《论粮食税》中特别指出1921年苏联经济的两大重点:一是继续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用国家资本主义挤垮和控制私人资本主义。二是把小生产和农民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
经过“战时共产主义”后,列宁领导革命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向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做出让步,解决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同时用新的手段加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手段不但包括了进一步加快国家所有的大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包括了大规模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苏联的经济,还包括了向外国资本出租和出借国有的矿山、工厂等等。1978后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不是有飞蛇走线的历时性联系?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教科书上说,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成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之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如一位朋友所指出的“当时党的政策是使民族工商业紧快走上一条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即计划定货、加工定货、统购统销、委托经销,公私合营进而实行全行业合营的道路。这有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9月7日的谈话为证”(胡德平)。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在《大祸临头及防止之法》指出:“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那么任何起义也不会创造出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是历史梯子上的这一级,即从这一级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是没有任何中间级段的。”
根据列宁这一“历史梯子”的论断,那么现阶段,中国和外国资本家合作经营的企业,包括当前国进民退“混改”,也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至于离“社会主义那一级”还有多远,起码是需要探讨的。至少,只要提高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国家能力),人均落后并不重要的经济模式,不属于“社会主义那一级”,而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政府重商主义(政府货殖主义)。1990年代中国政府重商主义或权控市场经济的思想要义,是强化国家(政府)“汲取财政的能力”(参看胡鞍钢、王绍光《中国国家能力报告》,1993)。正如独立评论人袁剑所指出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中国的变局》1995)。决策者在这一思想默契下,中国式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主导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亦即所谓“渐进式改革”成为可能。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实内涵。这里的“社会主义”,等于“政府主导”(国家主导),这里的“市场经济”,在“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法定条件下,仅仅剩下“效率优先”。
纵观全球,一切为了“提高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国家资本主义,确实绝无仅有,把它称之为“中国模式”也未尝不可。这样一种“经济模式”完全超越了经济范畴,当然是现行经济学理论——无论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老结构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老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中国特色利维坦(Левиафан)。所以,我勉强称之为“政府货殖主义”(政府重商主义)。因为它可以让交易对象(本国企业和居民)、贸易对象(外国政府和企业)提高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一句话,这种以整个国民、国土、社会生態背负为代价的“权控市场经济”模式成功的秘诀在于:不但可以置公平正义、法治秩序、国民待遇,乃至自然环境、社会历史、道德规范于不顾,而且,让政府行为和组织机体无限膨胀,乃至城乡社区生活凋敝而趋于社会原子化;不但可以让失去以土地为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本国国民,成为权力资本无限欺压盘剥的对象,而且,能在现行世界贸易中发挥政治比较优势,赚得盆满钵盈。
但问题在于,这种“政府主导,效率优先”的国家资本主义,既然是以整个国民、国土、社会生態背负为代价,就不可避免地要遭遇自身的极限。正如袁剑指出,这种把政权合法性与经济表现相互捆绑,而不是“努力重建政体本身的合法性”将可能遭遇“奇迹的黄昏”(2004)。而且,非经济学家秦晖也看到“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2008)。只要对中国政府收入(财政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收入,各种预算外收入、彩票收入、汇率差价收入除外)增量占GDP增量的比例分析,得知:占中国人口比例15.4%-16.14%的2.16-2.26亿吃财政饭人数+领取养老金人数消耗掉当年54.30%的GDP增量,剩下84.6%-83.86%的人口只消耗45.70%的GDP增量(2017)。难怪原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研究员陈申申一再呼吁“建立预算制度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由此可见,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國家”,可谓人类20世纪最大的奥威尔式谎言,沒有之一。因为这一谎言,最大限度地破坏了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不仅让左派和右派无所作为,而且政府推动的所谓渐进式改革失去内生性动力而断裂,对内葬送了中国作为转型国家的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最大限度地损害了国家形象,不仅差点毀掉中国,还将继续把中国“国内矛盾稀释到全世界”,终归会招来国际社会的敌视。以马克思主义观之,“提高财政汲取能力”为目标的集团官本位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其权力(中国“官粹、官僚、官家”特权文化使然)与资本(西方工商文明使然)勾兑杂揉的“中国模式”,已经造成“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矛盾”。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追求财税增长远高于GDP增长带来城乡失衡、社会失衡、央地失衡、内外失衡等广义生態背负问题的根源,当然也是中国大陆所谓官员+智囊型经济学家们的问题。我这里说的经济学家们,当然包括“50人论坛”及希望挤进该论坛者。不过,9月16日该论坛20周年纪念会的基调,已经开始正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有所改变(林毅夫、胡鞍钢两位除外)而重提坚持独立市场经济和法治环境。我对这一基调性转变,给予高度评价!
针对“北京论坛”《中美县级机构对比表》显示,美国县级政府机构为19个,中国县级政府机构为196个(截止2018.5)的“政府臃肿”及“官多为患”(张全景)“官满为患”(刘锡荣)的问题,我欣喜地看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和“50人论坛”上独具慧眼地提出了“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特别是“减政”改进办法:“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针对“运动治国”“指标治国”“文件治国”的问题,需要确立“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社区经济”三大经济形態并制定相应的《官法典》、《民法典》、《刑法典》以确立各自的事权边界。
针对19世纪以来人类特别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纠结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意识形態,造成诸般历史性悲剧的情况,除了从产权理论加以重新厘定,还应当超越现行工程货殖学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将“人权、事权、物权”整合为“共生权”范式,加以解决。
一句话,只要是“国家政权与资本的结合”,并“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经济”,包括“盐铁”“烟酒油电”专营、“土地(财政)金融”、“外汇管控”等,就可以叫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叫“权控资本主义”或“官粹资本主义”或“政府重商主义”更恰当,包括权控政府(国营)经济和权控市场(民营)经济,前者必然导致垄断,后者必然导致腐败,是事实,也是应当承认的常识。
在中国,改变特权导致垄断与腐败两大毒瘤的“权控资本主义”逻辑最有效办法和力量,依然要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一边完成自身“革命党-执政党-服务党”的改造,一边积极主动扶持中国社会成长,重建社会,为实现社会再平衡创造条件,以超越官粹主义与民粹主义二元对立格局,在国家政体上建立起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动态平衡机制,从而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克服原子化社会(官民)在权控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面前的无助、无奈、无力及无方向感、无安全感、无尊严感,并将这一过程用宪政共和制加以巩固(参看钱宏《再访问遵义,刍议“习近平精神”》,刊《经济要参》2015年第4期;《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刊2018年9月19日《经济要参》)。所以,改变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或权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態方式,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世纪钟摆困境”,势在必行。
这就是我说的中国的改进空间。套用毛主席的话说,“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宪政共和制的社会主义“三大要素”
分析完资本、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及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化”、“资本社会化”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历史运动之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共和制”的历史沿革和当代使命。
首先,从词源上看,society,严复把它翻译为荀子讲的“人能群,彼不能群”的“群”,后经日本转译为一个双音节合成词“社会”,社,即“团体”,会,指“用来聚集的地区”,组合起来就是“在一个地方所聚集成的一个团体”。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并不是脱离个人的行动的实体,在个人行动之外,并没有社会的、作为一个行动实体的存在。我们能够观察、记录、分析的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所以,马克思发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而“社会优先”中的有生命的个人,是社会的终极价值。这也是安•兰德在《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两本改行量仅次于《圣经》和《列宁选集》的哲理小说中表达的观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他并没有说“人的本质在其可能性上”是什么。
以共生哲学观之, 这个可能性,就是有生命的你、我、他“仨人”(相对于“仁人”),聚集于一个特定时空协和一致的合作行动,由这些协和行动形成的全部复杂而多边的分工合作,我们把这种分工合作关系的实时组合,称之为社会。因而,正如把“资本”放在优先位置的思想行为,叫作“资本主义”,那么,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的思想行为,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
那么,从政治上看,社会主义本身就等于民主、自由、共和体制的共襄生成;从经济上看,社会主义就等于社区、市场、政府形態的共襄生成;从文化上看,社会主义等于亲缘、地缘、生灵缘机体的共襄生成。在这个意义上,继政府论、自由论、资本论之后的社会论,就是共生论。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现实意识形态争论中,人们往往把社会主义与民主、市场、自由对立起来,或者在“民主”前冠以一个“社会主义”的定语。我认为,正如“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个伪命题(2006)一样,“社会主义民主”也是一个完全不成立的命题。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在我们国家传统的理解上和几十年的实践过程看,众所周知那个“社会主义”,影响较大较深的无论是从苏联式的“共产社会主义”(实际是国家资本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跟“民主”几乎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一层意思是,大家从思想理论上和历史起源上看,其实社会主义本身,又是最讲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1832)的兴起与民主运动(第二国际)、民主革命(欧洲1848)、人民革命(中国1949)的兴起,几乎是一脉相承。
正因为如此,后来很多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国号中,都直接打着“民主”(包括“人民”)的字样。比如“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柬埔寨民主共和国”、“ 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东德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北朝鲜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别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国号,“苏维埃”(Совет,Soviet)即是“工兵民主政权组织”引申为“人民民主”之意。
这都很说明问题,即社会主义就等于“人民当家作主”,即民主,等于“人民中心”、“社会优先”。所以,只要了解了社会主义的本义,也就了解了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与民主制,是现代政治文明制度的一体两面。我这是从思想理论上、逻辑上、历史起源上讲的。从传统实践上讲,人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却又恰恰相反,又把它与民主变成对立的东西。特别是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使用这类国号的国家是不是名副其实?这正是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引发包括特朗普所谓“抵制社会主义”在内的诸般概念混乱情况。
那么,什么叫社会主义?我的理解,第一,不能离开它的历史起源,即1832-1848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或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诉求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共襄生(成)长。
第二,就是以“社会”为先决条件,为优先条件,把“社会”放在第一位的这样的社会优先的主义,才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相对于“国家主义”、“朝廷主义”、“政府主义”、“资本主义”而言的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的天然本质,就是讲民主的。没有什么单独还要叫一个相对于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同义反复。
第三,在宪政共和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生成三大基本要素,一是有一种能够表达“社会优先”公平正义的概念,以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替代单纯公有与私有、官粹与民粹二元对立的产权理论(众人之私即是公,一己之公即是私,化解公私冲突,唯界定共生权法);二是在政治形態上,有一套能够实时表达公平正义“共生权”承诺的法治参与形式——实施民主自治程序的机构和公民实践;三是社会主义在经济形態上,要求一个当代正常国家,无论是以市场(自由)经济为主,还是政府(规划)经济为主,都应当建构一种作为生活托底的社区经济形態——以作为人民、国民、公民休养生息最大化的保障机制。在中国,更需要从企业所有制(如国营、民营、合资、独资)划分企业是否社会主义属性的梦魇纠结中走出来(参看钱宏《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即将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所以,社会主义“三大要素”,也是无分阶级、族群、官民身份地保持公民对当代国家信念的基本保障。
前面说过,“专制制度、民主制度、共和制度等国家政体形式,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相联系,反而是这些制度本身决定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优劣好坏。”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桑德尔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存在理由是“赋予不在阶级体系上层的人们、工人阶级和普通男女以权力,并且培养一种团结意识和对公民素质的理解,正是这些让整个社会都感受到我们是休戚与共的一个整体。”然而,以此观之,无论是欧盟,还是主权(民族)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和俄罗斯,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桑德尔在2016年6月谈论“脱欧论者和特朗普的能量源”时指出,既注意到社会民主党,把民主玩成一种政治自治工程以至成为“无法控制那些支配我们生活的力量”,又注意到丢掉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危险。“上一代主流政党的最大失败之一是没有能严肃看待民众的渴望,没有直接回应民众觉得自己在塑造支配其生活的势力方面有发言权的诉求。这部分是民主问题:民主在实践中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与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密切相关。失去权力的无力感部分就是自治工程失败的感受。”致使人们普遍对政治、政客、现有政党感到失望和沮丧,因而“对大部分人来说,政治没有能解决最重要的和公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什么构成公平正义的社会,以及公共利益问题、市场角色问题、作为公民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参看吴万伟译Michael Sandel: “The energy of the Brexiteers and Trump is born of the failure of elites” BY JASON COWLEY)。这也是我在本文开头,特别提出“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不要忘本”的原因。
相比之下,我感到福山先生在他的“历史终结”(“‘终结’是指‘目标’而非‘结局’”)于自由民主制的论断,遭遇现实挑战之后,提出“身份认同”的利弊以及“国家认同”作为补救措施,既在哲学上有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古老箴言,也对“世界社会”、“社会优先”的社会主义概念缺乏足够的关注与创新动机。
创新首先是经济形態、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的创新!
当官员和主流经济学家们还在围着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调整“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和“物流智能结构”作产业结构规划转圈圈,又摆脱不掉“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的周期性危机,在为“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官粹主义还是民粹主义”“资产国营(大家族)化还是资产社会(民营)化”纠结,在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国企经理人的信托责任还是体制问题”引经据典调查研究,在为“城市中心论还是乡村中心论”“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孰轻孰重”争执不下之时,中国、美国、欧洲和南部非洲的“社会人”,早已针对中美欧非各自的问题——中国存在“城市病”“乡村败落”、美国存在“城市空心化衰败及中产阶级失落”、西北欧洲存在“福利国家惰性病”和南部非洲存在“种族特权”及其一系列关连问题——开始用脚呼唤和发动另一场既非“市场经济”又非“政府经济”的经济实践,这就是有点类似上世纪70年代韩国“工农业均衡发展”的“新村运动”,却又赋予新文明新经济形態意义的美国“新经济运动”“乐活经济运动”、欧洲“生態村与生活社区运动”、南部非洲“班图精神运动”(生活在一个Ubuntu社区里,必须彼此分享和关爱Live in a ubuntucommunity and must share things and care for each other),以及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生態经济运动”“新上山下乡运动”“环保酵素救地球运动”和“共生思潮”。
美国的“新经济运动”,欧洲的“生態村与生活社区运动”南部非洲的“班图社区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新上山下乡运动”“环保酵素救地球运动”和“共生思潮”,虽然目前都远非主流,而且,既不同于城市化发展“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也不同于网络化“城市社群联通派”和“PPP广义智慧城市派”的政策思路,而具有了真正“新经济形態”——社区经济意义。很可能是人类走向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一个大方向(参看《谈谈社区、市场、政府全息经济形態的哲学品位——兼谈哲学对象的划时代转换》,2015)。
总之,按照“社会优先”的社会主义,起码必须“有社会”,如果没有或不充分,国家和政府就有责任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也要积极主动扶持社会成长,重建社会,而且“社会优先”,才可望在“政府经济”与“市场经济”二维中引入第三维——“社区经济”(顺便说一句,在中国,为了鼓励城乡居民自组织就业和创新,鼓励承载市场经济、政府经济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般的社区经济形態成形,我主张象20年前上海市扶持国企下岗职工实施的“5040工程”那样,减免所有年利润100万人民币以下“小微企业”的税费),包括“草根的生態经济运动”所蕴涵的经济社区化、社区服务化、服务生活化——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结构,即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局面。倘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作为工商文明后发的国家,就可能成为生態文明的先发国度。
我们需要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
我们说,“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是指他要十分清晰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优先、公民本位的社会主义,而非“无社会”的精英本位的“假、大、空”社会主义,甚至也非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式企业本位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参看钱宏《以社会建设为中心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录《中国:共生崛起》P160-165,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Social priority的社会主义,是在生態文明的全球化时代,美国式“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发源地)欧洲式“民主”社会主义的升级版——整合了洛克“政府论”、马克思“资本论”、新世纪“共生论”与东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古老智慧的社会共生主义,亦即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Global Symbiosism with Social Priorities)。
早已从英国手中接棒“世界领导”责任的美国,不可能回到“门罗主义”。美国总统要在生態文明的全球时代,继续承担引领世界的责任,就必须意识到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才是“必须捍卫释放人民身上不可思议的潜力,使一切成为可能的基础”,也即是全球共生主义的基础。从而区别于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特别是以某个“Party-state”为基础的全球主义和某个“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全球主义,并加以避免。
如果既非“白左”又非“普右”又在竞选中与民主党互换车道的共和党人特朗普,真的要介入国际社会意识形态新建构,只要高举起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旗帜,就能不让英联邦人民失望,不让尚未完成工商文明社会转型又跨着生態文明的门槛的亚非拉人民失望,更不会让美国人民失望,还能重振民主社会主义的欧洲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及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信念,让人们找到历史感,让一切“无社会”的假社会主义原形毕露无所遁形,而自觉改弦更张顺势而为。
假如特朗普真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且强迫它脱下旧时代的伪装”(基辛格)的历史人物,他就应当意识到,丢掉全球主义,不从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的新思想,谈“改革国际贸易体系”和“选择独立与合作而不是全球治理,控制和统治”,在逻辑上存在很大缺陷,使自己陷入现实利益困境(比如与中国打贸易战,与盟友争吵)。这还不只是放弃责任的孤立主义美国凭什么再次强大的问题。哈耶克指出,人类合作是社会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民主、共和、市场、社区、地缘的优点,就是它使我们能够相互合作,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威权风格的、自顶而下的规则,不是秩序或进步的源泉,相反是一种障碍。不同个人、社区和企业群体、市场、地缘国家等不同主体间能够贯彻民主、共和、相互合作,就能实现因“信息相互融合而发生知识的质变、升华”,进而不断打破和修正威权风格的、自顶而下的规则。因而,单个人或单个国家或地区不能以一种自给自足或与世隔绝的方式生存,追求自给自足或与世隔绝是反社会性的,更何况今日人类社会因互联网云计算而去轴心化已成大势。
那么,顺势而为,体行共生,势在必行。正如《理性乐观派》和《自下而上》两书作者马特•雷德利(Matt Ridley)在《奇妙的“云大脑”——这就是市场》中所说,哈耶克1945年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指出,中央计划无法发挥作用,因为它试图用某些精英或领袖个人无所不知的才智,来取代人民弥散的、碎片的、本地的、但又相互关联的知识,大部分这样的知识是默会的,或者说是自组织整合的。正所谓“必集大成,方得智慧”。如果说,把前者叫作“官粹主义”,那么,后者自然是“民粹主义”,而这种民粹主义不正是自由、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社区、市场、政府经济形態所必备的社会条件吗?怎么就不“政治正确”了?而以“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进行“改革国际贸易体系”和“选择独立与合作而不是全球治理,控制和统治”,一切就顺理成章(而且在“双边”“多边”谈判的运用上,也将更加灵活而有效,也不会拘泥于“双边”或“多边”)。
只有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才能与去轴心的全生態(区块)链社区、市场、政府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现实相匹配,承载得起各个主权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交流想法、服务社会从而激励社会变革,“追求自己独特的愿景,建设自己充满希望的未来,追逐自己对命运、遗产和家园的美好梦想”,真正体现“这美丽的星球上每一个国家都很特别,每一个都很独特,每一个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闪闪发光”,从而共襄生成繁荣、发明、文化实验与可持续和平。
总之,人类需要创建一个“千灯互照、光光交澈”的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的全新生活方式——重建世界秩序(参看钱宏《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繁体版,晨星出版,2018)。
陽子2018年9月26日初稿10月6日成稿
作者:钱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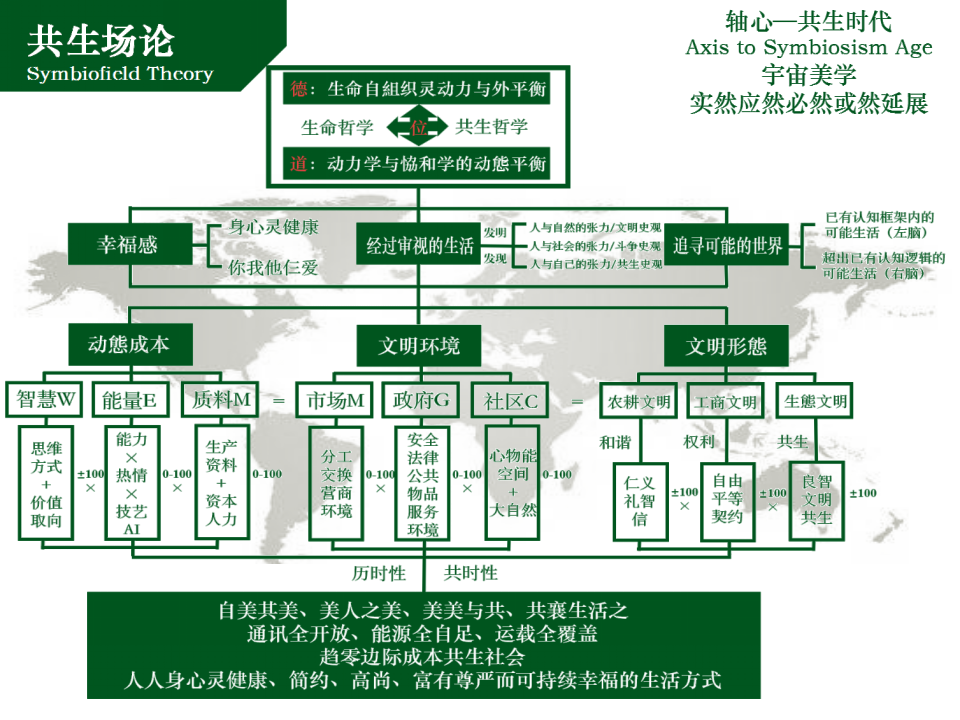





您好!请登录
已有0评论
购物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