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Articles
-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2026/02/24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2026/02/24【共生经济学·前言】 经济学的认知偏蔽与分化催生新思维 The Cognitive Bias and Fragmentation of Economics as...
-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2026/02/22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2026/02/22《共生经济学》自序 如何面对“终极的免费午餐”? How Should We Face the “Ultimate Free Lunch”? 一、从宇...
-
 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2026/02/17
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2026/02/17全球共生范式下的现代正常国家 Modern National Normalization under the Global Symbiotic Paradigm ...
-
 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2026/02/16
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2026/02/16论殖官主义:政权更迭为何不能终结人民的苦难? Chinese Reproductive Officialdom: Why Regime Change Has Not...
共生思想理论前沿
THE THEORY
-

-

-

-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Symbiosism:Charles Thomas Taylor &Qian hong又一次量子缠绕...
查看详细说明
Speech
-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 ——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钱 宏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语从金音玉(Yǜ):金口玉言,一诺千金,性人诚恳、执信; &n...
-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点击播放 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访钱宏主持人:...
陈建利:专访钱宏:走向共生——中国的真实经验与当代使命
发布时间:2022/02/10 公司新闻 浏览次数:1121
钱 宏:走向共生——中国的真实经验与当代使命
陈建利
(访谈时间2010年11月于北京天通苑)

百多年来的复制选择之争
陈建利:我最近又读了你2007年出版的两本书,《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和《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我看大部分内容,收录的都是你在美国的《New World Times》开的专栏文章。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你的思想,你会怎么说?
钱 宏:走向共生。不管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从纵向上说,是从狩猎采集文明过渡到农耕文明,然后到工商文明接下来是生態文明,或叫“共生文明”——共生(Symbiosism),或者说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是生態文明的灵魂。
一百多年前,中国还处在农耕文明之中。之后是被动也好,主动也好,中国开始复制和选择复制西方的工商文明——实行民族自立、国家现代化、个人自由与社会自治。开始是不肯的,后来发现不学习不行了,从曾左李张,到康梁,甚至慈禧,到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然后到五四,到蒋介石、毛泽东,其实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主客二元对立统一求同存异思维和价值取向——为了为我所用的“选择性复制”在打架。你要选择这一块复制,我要选择那一块复制,错综复杂,为了选择复制的不同而打架,一直打到1949年,以一方的胜利在大陆成立PRC,而另一方退守几个岛继续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的ROC实验,暂告一段落。
而后,PRC开始了在传统与现代、苏联模式与美国模式间的选择复制,从1950年代的工业党与农业党之争,1960年代的功过(天灾人祸)之争,1970年代的资社之争,到邓小平及后邓时期,至当下的左右、公私之争,莫不如此。
所以,当代中国人,必须在思维方式与价值观上,从基于主/客、你/我利益立场的斗争思维(包括革命战争思维、特权敛财改革思维“双革思维”),转变到基于你、我、他生命自组织连接平衡再 平衡的共生思维上来。

陈建利:若能简单地复制倒也好了,关键是不得不在原来的农业帝制文明下嫁接,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我看你曾经在1991-1996年主持过国家八五计划重点工程《国学大师丛书》(出版二十八卷本),该丛书还获得国家图书奖,特别是你为丛书写的总序之一《重写近代诸子春秋》,得到学界广泛好评。这说明你对中国历史新旧之交的文化心理过程,比较熟悉。既然讲到“中国的真实经验”,那么,你能说说这个真实经验的内在逻辑演变吗?
钱 宏: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并不是偶然的,其社会历史逻辑,是有效地顺应了当时社会的三大诉求。一是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这一小康社会的基础诉求;二是城市部分中小工商所有产者“反垄断”的经济诉求;三是受五四精神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以及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青年“崇尚科学、追求民主”的政治、文化诉求(其不足是忽略了“自由与法治”的基础性,这个先不说)。但解放之初的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小所有者的国家。从欧美国家从农耕文明过渡到工商文明的历史轨迹看,发展工(商)业文明首先就要有大量的资本投入。加上当时苏美两大政治阵营已经形成,且由于朝鲜战争,在斗争思维的支配下,中国大陆客观上别无选择地“向苏联一边倒”,从而脱离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运行体系。
当时的大陆PRC新政权,又面临一个重新选择!不是选择复制,而是选择“是回归和维护以小所有者为基本构架的状态,还是要进入到工商文明和主权国家框架?”
其实,毛泽东更多地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同时感情上是站在小所有者一边的。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其思想、哲学属于西方文明中反垄断的一支(马克思主义),再来,它本身也是工业文明诉求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成员,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都到过欧洲或苏联,受到西方教育,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对美国20世纪初的“反托拉斯扶持中小企业的进步主义运动”缺乏了解,他们主张搞工业化,却又把“公有制”与“私有制”对立起来,认为“小所有者”和“民族资本家”一样,都是要被改造的私有制;另一部分人,如邓子恢等则倾向于前者。在五十年代,中国上层就有一个“工业党”和“农业党”的争论。加上苏联赫鲁晓夫给中国提供156个配专家也带部分资金的工业项目,结果是毛泽东转向支持“工业党”,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需要资本,而作为后发国家又无海外殖民掠夺或贸易输入资源的可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农民(小所有者)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一系列问题,可以解释为什么爆发那么多政治运动,包括反右。它的目的就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布局。包括后来的“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都要从中国要进入工商文明,要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整体合理性来解释,局部看可能是很不合理、不人道的。当然,不是说整人、饿死人是对的,也不是说这是唯一的方式。但当时执政层决策者们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就是如此。
陈建利:这是一种大历史视野的观察了。
钱 宏:我说的是中国的真实经验,后面还要说当代使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完成了基本的工业布局,特别是军工建设,最大的成就是“两弹一星”。但民生这块萎缩了,社会自组织力没有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种单向发展,加上后来又和苏联闹翻了,自我循环不下去了。前三十年基本是模仿苏联,实质上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列宁和毛泽东都说得非常质白),与欧洲经典社会主义(也叫民主社会主义)关系不大——2005年上层精英有一个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我也写了一篇小文,大意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是必要的同义反复”,我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缺失了主语“社会”的主义,是当权者套利的大箩框——什么东西对其有利有的没的都往里装,很方便“选择性执行”或“选择性搁置”,反之,就贴上某种标签,加以阻止甚至清除!
这后三十年,显然要补民生成长的课、补重建社会的课了,但是共产党并不是马上就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任何国家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当时,中央财政已严重不足,一批又一批的转业干部进入地方,要靠地方财政来支撑,地方财政从哪来?当然是人民、是社会中汲取来!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搞起了后来说的“改革开放”。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中国历来的改革或变法,从商鞅到王莽,从王安石到张居正,直到当代,出发点都是为了“官生”,而非“民生”,但这里又有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如果民生太差,官生状况自然好不了!农民没饭吃,所以才有安徽小岗村的试验,没有钱,才有深圳特区,这些一个一个的点,慢慢连成一个面,背后的逻辑是相通的。最后,通过政府主导型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渐进式改革”——包括1984年表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92年表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管它叫“权控市场经济”,也可称之为“半统制半市场经济”——回避“孰公孰私”的根本问题,这是中国大陆的一大政治欠债,终归要还的(前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有幸遇到高尚全先生时,我把这个观点分享给了他)。

2008年10月25日钱宏与社会转型大师高尚全先生改革开放30周年高层国际论坛上有幸相遇,并把自己对“渐进式改革”持保留观点告诉先生,高先生很严肃地听完,正要说话却被会场其他人打断了
如果到此为止,尽管有“土地财政”的积极推动,当代中国的改革,很可能还会随时夭折,走回头路。但是,这一次和历史上所有变法、改革,有一点不一样,就是部分引进了经济学上讲的“制度外部性”,邓小平说过所谓开放,就是对美国开放,也就是部分引入“制度外部性”,这一点非同小可!由于“制度外部性”的进入,恰逢经济全球化运动,中国经济进入金融资本为杠杆的城市化、外向型发展历史进程。这其中,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国家,降格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WTO),堪比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156个工业项目,对中国形成基本工业布局的影响。
虽然在《八二宪法》名义下形成“全官寻租化、全民佃农化”,以及对欧美开放的局面,取得了“多重两极分化”的失衡性总体经济成就,避免了他对毛描述的“军阀混战”,压制了“左右资社之争”,但其“全官闷声发大财”的背后,是深入中国底层人民和中国社会骨髓的“世纪之痛”!

这里我不想多说,我只说一点,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确是取得三十年的高增长,GDP总量已经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而且,只要不脱离WTO体系,很可能不久就要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但同时,也积累了高昂的社会成本和沉重的生态背负。因为,在“权控市场经济”模式支配下,形成了一种“全官寻租化”和与之相应的“全民佃农化”格局,这就使得当代中国社会进一步原子化,以及包括贫富、城乡、区域上的失衡性“多重两极分化”,有别于西方“阶级矛盾”的传统中国的“官民矛盾”两次凸显——前中组部长、前中纪委副书记分别以“官多为患”(1998)和“官满为患”(2010)加以形容。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叫“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凸显!
中国当前应以“社会建设”为中心
陈建利:你说“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中国现在是否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向工商文明的转型?
钱 宏:你说到这里,2007年9月7日,中央舆情局委托上海社科院,就17大报告最后一次征求上海社科界意见,可能因为我在《New World Times》开的专栏被有关方面注意到,所以邀请我这个既不是上海的,也不是社科界的人,参加“上海社科界代表座谈会”。主持人表示请大家放开表达意见,轮我发言时,我就讲了一个意思,即中国三十年前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后三十年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现在开始应当实行“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整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社会建设”,甚至“重建社会”的历史阶段。这实际上是补“社会主义”的课,即补上“没有社会”或“社会缺位”的社会主义的课,你懂我的意思。参加那次座谈会一共9个人,除我之外,都是上海社科界的名流。大家的发言公开选登在9月28日的《社会科学报》上。而且,17大政治报告发表后,我们看到的确把“社会建设”写了进去,当然,这并不一定是听了我一个人的意见,很可能还有很多其他人士的意见。

2007年4月,在上海淞江区考察“政府诚信”
前面说过,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程,必须实行民族自立、国家现代化、个人自由与社会自治。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完成国家基本工业布局,另一个是完成了基本民生和金融资本的课,中国政府现在有大把的钱,但社会建设滞后。后三十年的经济补课带来的问题,并不比前三十年少,问题反而更复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政权最根基的部分有问题。我写了一篇文章《上梁不正下梁歪与下梁正上梁歪不到哪里去》,拿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做一个比较。一个是社区及自治组织;二是各种志工组织和非公募基金会;三是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还有乡镇自治政体。对比发现,这些“下梁”,中国是几乎谈不上有的。
所以,要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中国接下来就是要完成社会建设,实行社会再平衡。因为中国的基础社会结构,以前叫乡绅社会,近代以来被摧毁得干干净净;乡村生活又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被“土地财政驱动下的城市化运动”冲得七零八落。如果说有一个健全的基层社会,下梁是稳定的,就有能力来消化国家发展甩下来的包袱。现在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像1978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样,转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上来。2003年新班子上台,我特地写了一篇长文《从“三个代表”到“社会元勋立宪制”:从中共“集体理想”与“利益集团”矛盾运动看中国未来四种可能的前景——答中共中央机关报理论版负责人问》,我要说的是,当代中国既不可能回到“君主立宪”的路数,也不可能回到“特权专政”的年代,但又必须“重建社会”,必须实行主权在民的“宪政秩序”,哪怎么办?我就提出一个“社会元勋立宪”的概念,也可以叫第三种道路。所谓“社会元勋”,就是为中国重建社会立下最大功勋的人。
中国像一只凤凰,它应以率先全球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为尾舵;这凤凰的躯干,就是社会建设。现在有这么多钱,要有意识地、积极地扶持社会组织的有序成长,骨架、经络、八大系统和五脏六腑结构、功能健全,中国才真正会稳定,不会出大乱子了;然后以政治体制改良和经济结构变革(创新)为两翼,带动全身起飞。那么,什么是这只大鸟的凤头呢?就是以人类的共生法则、共生智慧为新型价值观,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包括不同社会群体、组织和不国家、民族、地区)、人与自己身心灵三大关系。
我有句话,叫“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就飞起来了,既有方向,又比较平稳。这就是我说的“当代使命”。
陈建利: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大的局势判断,就是中国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钱 宏:从戊戌变法到现在的一百多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革命,继续革命和告别革命。毛泽东说自己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解放了中国大陆,第二件事就是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这三十年是告别革命,搞经济建设。现在中国处在爆发第三次革命和走向共生之间的一个历史性选择的阶段。爆发第三次革命是指,延续以前两次革命,完成没有完成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政治体制改良、经济结构改变、社会建设创新在内的社会有序大变革。
这个阶段如果引导的好,可以走向共生之道!这是一次真正的社会转型,如果转得不好,不成功,或者陷入“转型中期陷阱”,不是改革的成果会不会丢失的问题,我非常担心的是,又会爆发一次社会大革命,而且其惨烈程度,很可能超过法国大革命,对世界经济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冲击。所以,如果中国必须崛起,就只能是“共生崛起”。
陈建利:共生是另一个可能的选项?我记得你2009年还自编了一本内参《走向共生·高端报告》,一共想做十八期?
钱 宏:对。为什么要走向共生之路呢?走向共生,也叫“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的历史跃迁。因为西方现在的工商文明也遇到了困境,现在也出现了问题, 走向了极限。因此我才从自己的观察、体验、反思、探索中提出一种“共生哲学”或叫“共生新思维”。
第一个极限,是“增长的极限”,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汽车工业、航空工业、火电业都是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按照这样的路子增长是有极限的。1968年成立的“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发表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此有充分的论证。
第二个极限,是“对抗的极限”,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状态之中,工商文明和之前的大部分文明,建立的都是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一过程中,势必是把传统的地缘政治作为国际关系的主导。然后,对自然也是一种改造、掠夺的态度,对自己是不断地挖掘自己、处于一种对抗的、精神紧张的状态中。原子弹发明后,人们已经发现,地缘政治已经走到极限,对抗不下去了,因为打起来没有赢家。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肯尼迪让赫鲁晓夫把导弹体面地撤走,苏美也开始了限制核武器的谈判。
第三个极限,是随着工商文明进入第五次科技革命,带来个人能量的提升,我把它叫做“施恶操控的极限”。工商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展速度、数量、复制效率。第一表现在交通方面,公路、高铁、大型喷气式飞机的民用,缩小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空间。第二个是互联网、手机、IT业的发展。过去文明状态下那种支配性的权力关系,之所以能畅行无阻,就是统治者或强势集团“坐拥资源不对称、权责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现在这些东西正在打破,尤其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愚弄、误导人们视听的统治伎俩,越来越困难。一方面,信息不对称的统治基础在逐步迅速瓦解,另一方面,统治者或强贵集团坐拥资源不对称、权责不对称的优势依然不肯松懈,虽然不排除他们利用数字技术,对人们进行“隐私控制”和“局域网(防火墙)控制”的可能。
但这个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能量,总体上在迅捷提升之中,过去那种强者无视弱者死活的情况,将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甚至人类都难以承受的后果,也就是施恶也面临极限。假如一个17岁的小伙子没有得到善待,同时,他恰巧又是一个IT天才,他凭自己小小的个体的力量,就可能摧毁五角大楼的终端,摧毁中央情报局和中央军委情报部的终端,甚至进入最高领导人最高密级的核按扭控制程序,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这就是“超限战”,想想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况!所以说,必须善待一切生命,善待每一个人,不管关系亲疏远近,不管身处强弱多寡顺逆。
三大极限摆在这里,人类就要重新开始反思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现在面临的三大极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代全球面临的主要矛盾。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
和解,才能重塑中国魅力大国形象
陈建利:这怎么讲?
钱 宏:这是从社会哲学上讲的。生态文明是要在这三大关系上摒弃过去的权力关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要建立广泛全面的互助关系、伙伴关系,以至于共栖、共济、共生关系。过去的支配关系的哲学基础是“达尔文主义”,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从源头上就是有缺陷的。就在达尔文提出他的演化论的时候,在德国和俄国另外一批生物学家,俄国三个植物学家和德国的一个生物学家,他们研究生物在演化过程中,互助性远远大于互斗,互助、共生是一种主导关系。生物从最初的单细胞越来越丰富多样,最后形成地球生态圈,这才是符合常识与感知经验的事实。俄国社会学家克鲁泡特金写了一本书叫《互助论》,就是根据那三个植物学家的共生理念写出来的。中国的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同时,他总结了世界上各种学说,基于此,他写了一个《政治互助论》。
上世纪初,美国有一个生物学家也写了一个关于共生的书,但影响不大。真正影响大的是玛古利斯,她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根据前人的研究、经过实验室实验取得确凿证据,总结出来“共生起源”的概念,她提出来以后,达尔文主义者就有些恐慌。新老达尔文主义者和她展开论战,论战持续二十年,从70年进行到89年前后,最后玛古利斯的共生起源的概念被接受,写进了生物学的教科书。共生起源,还是讲的演化,延续了生物之间、种群与种群之间、种群内部互助的作用和价值远远大于互斗。共生是一个“共过程”的关系,强调的是一种状态,用一句英语短语说是“live and let live”。
共生主义生活方式是什么?第一是健康的;第二是简约的,低碳可以归到这个领域里;第三是高尚的,当年辜鸿铭反对向西方学习,其实他是从高尚生活和奢侈生活的比较的角度上讲的;第四是幸福可持续的;最后是富有尊严的。所以,叫作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从动力学角度来讲有三大动力,或叫三大自组织力,一个叫政府自组织力,一个是社会自组织力,第三个更本源的是公民自组织力。我们过去的三十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发挥了第一个自组织力,由于它过于强大,它抑制了社会自组织力和公民自组织力的发挥。所以中国还有很大的余地。
陈建利:你的“共生”的概念,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看人类的未来和现在的问题,认为以“共生新思维”指导中国崛起,也是中国树立负责任的魅力大国形象的需要。而对于中国接下来的转型,你提出要对内走向大和解,这观点很重要。
钱 宏:在选择复制的过程中,当代人受中国传统“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让当代中国结下了太多的社会仇恨。因为每一次每一种选择,都意味着利用政权的力量把一部分人打下去甚至杀掉,另外一部分人起来走向主导地位,成为既得利益者。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49年,到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四五天安门事件、将国企职工当作“不良资产”强行剥离和“国进民退”……等等,一波又一波,这些人其实都是中国人,仅仅冠之以“敌人”、“阶级异己分子”、“离心离德者”、“动乱分子”、“不良资产”、“私有者”后,就可以毫无心理阻隔地加以歧视,甚至可以任意杀戮,或者剥夺,毫不手软。
既然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而且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课题,那么,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也就亟需走向正常有序的状态,而不是继续依靠一部分压制另一部分这种斗争、专政哲学来维系。那么,这个“正常有序状态”的内在动力、政治资源和法理基础从哪里获得?以我的浅见,就是先要实行社会大和解,首先要在意识形态上用“和解哲学”取代“斗争哲学”。而和解,第一需要智慧,而不是谋略;第二需要笃行,而不是作秀;第三需要悲悯,而不是谁战胜谁,也不是谁对谁享有特别的支配权力。大家共享一片蓝天,而非不共戴天。
那么,中国共产党,最后必须完成一次超越“政党政治”的“革命党-执政党-服务党”三级跳式的伟大历史蜕变!
一个仇恨、斗争哲学思维浸润了一百年多的国家,如果形不成基本的“和解共识”,也就不存在,更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人类公共性的承载者)社会;而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就没有明晰统一而富有魅力的国家形象。
共生哲学发现,没有敌人,只有病人,若有敌人,就是自己!和解,表现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承认所有人(包括敌人,不分你我他)的生存权利,不以人为敌、以邻为壑,而以谋求共存互补共生为出发点;在政治经济上,不以谋求获得特殊利益的权力为政治目标,而是以追求契约和法律机会平等为基础。
社会和解的涵义:
第一,意味着国家真正承认所有公民主体间性共生权的地位,所有公民,谁也不是谁的客体对象(Object),也就是全体公民、公民、国民“交互主体共生”。
第二,意味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真现公民主权(人权、事权、物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里的公民,包括“官”与“民”,而公民主权,也许称之为集人权、事权、物权为一体的“共生权”,更恰当。反过来说,没有公民主权的实施,讲和解,无异于空中楼阁镜中看花痴人说梦。
第三,意味着所有公民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因为只有国民待遇上的平等主体(Subject),才能不分身份贵贱地讲和解。当国民被事实上划分为集团性(如党派)、地区性(如城乡)的权贵与草根身份差等时,用什么保障不会每天都将滋生仇恨、斗争这一和解的对立因子呢?
最后,和解意味着国家形象的历史性改变和创新——形成全体公民个人最大公约数认同的真正适应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需要的简洁、明快、相互连贯、谨记笃行的价值目标诉求,这就是建立在“善待他者”伦理基础上的“良智、文明、共生”价值观念。
总之,没有社会和解,就没有和谐社会,更遑论和谐世界。因此,我坚定地认为:对内实现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应当成为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的当代主题!
应当倡导一种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新的思维方式
陈建利:你从“社会和解”引伸出的“共生权”概念,非常新颖,值得好好研究。最后,你能不能再概括一下“共生新思维”的基本内容?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
钱 宏:前面说了,中国还要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这自然应当倡导一种与生态文明相适应,且能引导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的新的哲学或新思维方式——一种更具兼(包)容性、迫切性和前瞻性的 “共生新思维”(或者说“共生价值观”)。
“共生新思维”,也可以称之为“共生之道”,是不偏向、偏袒、偏信任何个人、组织、集团的思维;是将东西南北古今中外一切工具理性,置于生态文明价值理性的规范之下的崭新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国家观、政治观、经济观、文化观、哲学观;是继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与美国独立的民有、民治、民享之后,中国新改良贡献给世界的又一普世价值——良智、文明、共生。其内容有三:
一、共生新思维,是全生态社会建设的路径选择,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是不分强势、弱势、优势、劣势、精英、草根地善待(即无歧视地对待)所有人,是所有社会成员臻趋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襄生活的共生世界的法则。
二、共生新思维,是实现全社会大和解,彻底沙弥百年“斗争哲学”(革命、继续革命与告别革命行市场经济)带给国人自危、恐惧、忿恨的心理阴影,超越治乱循环的历史窠臼,让全体国民放下包袱,轻装回归休养生息的正常生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共生新思维,不是弱者说给强者的哀求,不是强者对弱者的恩赐,而是精神强大者、新生代主动伸出的和解之手。
三、共生新思维,旨在为发挥三大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开辟道路;是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中国政府穿越三大陷阱(泛中等收入陷阱、泛产业化陷阱、丘陵多山人口大国城市化陷阱),克服世纪性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道德失灵三重失灵,以及“市场滞胀”和“政府赤胀”危机,催生社会诚信互助,激励全体国民积极参与、勇于且善于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教育创新)的必由之路。
总之,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共生新思维”,或“共生价值观”——是创建一个能将“有生命的个人”精神体能及其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注入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尚书)、小康社会(荀子)理想内涵的共生世界;一个将中国与世界切实导向一种健康、简约(低碳)、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全新生活方式。
中华民族将以良智、文明、共生,会盟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有、民治、民享一道,普惠全球、全人类!
2010年11月15日
陈建利,南方都市报资深评论员
钱 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特聘研究员、全球共生思想力实验室

(参看钱宏著《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上一篇: 悲情预测背后的历史逻辑及因应之道
下一篇: 宏观世界之东方当大國者的小朝廷心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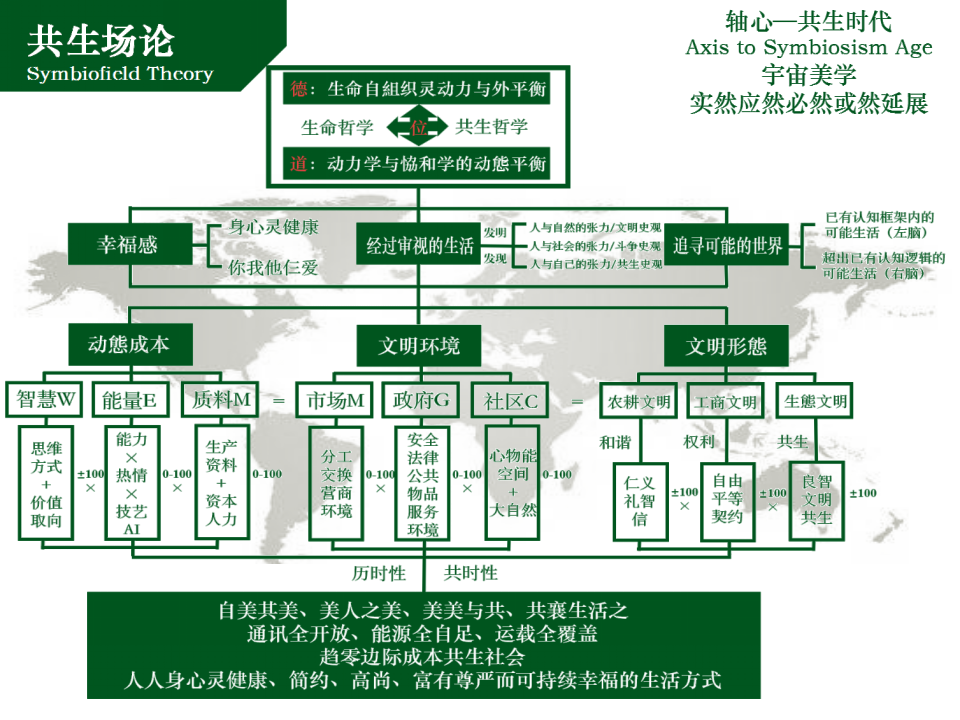





您好!请登录
已有0评论
购物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