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Articles
-
 AI三大瓶颈及其10个“傻白”和5个“傻精” 2026/02/04
AI三大瓶颈及其10个“傻白”和5个“傻精” 2026/02/04AI三大瓶颈及其10个“傻白”和5个“傻精”The Three Major Bottlenecks of AI and Its “10 Naïve Blind Spots” and “5 Cunnin...
-
 共生场图灵测试 (SFTT)的设计 2026/02/03
共生场图灵测试 (SFTT)的设计 2026/02/03共生场图灵测试 (SFTT)的设计Symbiotic Field Turing Test (SFTT) Design 本报告根据Google AI与Archer宏2...
-
 沃什、马斯克与钱宏 GDE 体系:把握宏观不确... 2026/02/02
沃什、马斯克与钱宏 GDE 体系:把握宏观不确... 2026/02/02沃什、马斯克与钱宏 GDE 体系:把握宏观不确定性的范式革命 Warsh, Musk, and Hong Qian's GDE System: A Paradigm ...
-
 从 GDP 到 GDE——如何切断“规模—外汇—互害”的... 2026/02/02
从 GDP 到 GDE——如何切断“规模—外汇—互害”的... 2026/02/02从 GDP 到 GDEFrom GDP to GDE——如何切断“规模—外汇—互害”的制度循环?How to Cut the Institutional Loop of “S...
共生思想理论前沿
THE THEORY
-

-

-

-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Symbiosism:Charles Thomas Taylor &Qian hong又一次量子缠绕...
查看详细说明
Speech
-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
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2021/07/08三大自组织货币的共生格局 ——宏观世界之数字货币 钱 宏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
新汉字yǜ的释义 2019/11/16语从金音玉(Yǜ):金口玉言,一诺千金,性人诚恳、执信; &n...
-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
钱宏: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 2019/11/16点击播放 中国的真实经验与未来走向《凤凰博报》专访钱宏主持人:...
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之结症
发布时间:2020/05/17 共生经济 浏览次数:901
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之结症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构性缺陷(摘要)
本摘要,摘自中美“贸易战”开打前两个月的2018年1月,发表在 “全球共生论坛”公众号(IGS1218)上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现实长项与理论缺失》。
一年多来,中美贸易战的结症,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美经济社会各自都有结构性问题。因此,都存在很大改进空间(参看钱宏:《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各自大有改进空间——写于福山《身份》将问世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之际》,人民网《国际日报》,而要改进,甚至改变,就要找到各自结构性问题的结症所在。这里讲的结症,首先是指经济学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
常识告诉我们,不能用跟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相同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由于林毅夫先生的特殊政治地位及其影响力,他所谓“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上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与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某些对应关系。因而,当我们开始着手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时,不但不能再沿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而且,必须对林先生经济学的结构性缺陷进行梳理。
以Symbionomics(共生經濟学)观之,新结构经济学当然也有其现实优长,然而,撇开新结构经济学的地域性“横向国别比较研究”、中国“区域比较研究”、城乡市农比较研究、社会阶层比较研究这些“结构遗漏”不讲,单就中国市场与政府、经济与政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定位而言,新结构经济学尚明显带有六大“理论缺失”。

2008年由高尚全先生介绍钱宏与林毅夫相识
以下为摘要内容:
“新结构经济学”否定了“旧结构经济学”的国别依附理论,却又不自觉地形成了自己的企业、公民(农民)依附理论。
所以,相对于“纵向国别比较研究”而言,尽管林毅夫先生作为独立经济学家,有着以“中国经济奇迹”为宏观分析基础,建立“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抱负,甚至在“帮”非洲国家说话和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做出了“把中国带入世界”的宝贵努力,特别是同时也有“帮”“政府、企业、农民(公民)三重客体”说话的拳拳之心,让人肃然起敬!但是,他的“新结构经济学”,在中国国内的“市场与政府”、“经济与政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方面,有着明显的理论缺陷,而在“区域比较研究”、“地理人文性地域比较研究”(含“横向国别比较”)、“城乡市农比较研究”,特别是“社会阶层比较研究”上,则有着明显的结构性遗漏。
撇开地域性“横向国别比较研究”、中国“区域比较研究”、城乡市农比较研究、社会阶层比较这些“结构遗漏”不讲,单就中国市场与政府、经济与政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定位而言,新结构经济学尚明显带有下列“理论缺失”:
第一,从法理常识上看,政府、企业、农民(公民)并非经济学家的“三重客体”,而是具有“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能力”的“三重主体”,即政府、企业、农民(公民)都具有法理“行为主体”即“仨自组织人”的经济学意义。所以,尽管林毅夫也把“企业自生能力作为新结构经济学微观分析基础”,但其在理论上超越现行经济的“宏经”与“微经”划分,未能在法理上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更没有承认公民(农民)个人的经济主体地位。
第二,从哲学上看,马克思说,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三重主体”只是强调政府、企业、农民(公民)的主体地位,之所以都有主体地位,是因为政府、企业、农民(公民)都具有创造历史的“生命自组织内生性活力与外连接平衡能力”而又非独存的主体。无论在经济活动,还是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会活动中,政府、企业、农民(公民)都是一种“主体间性”的相互作用共襄生活的过程。由此观察,我们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给出仨自组织人的定义,仨自组织人(Three Self-Organization Person),即行为方式上同时具有开放赋能(Open empowerment)的政治自组织人、经济自组织人、文化自组织人三位一体全人称(你我他)共襄生长特征的行为主体。理解这一事实和定义并不难,我们甚至只需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互助”理论(克鲁泡特金)、“创新”理论(熊彼得)和“铅笔的故事”(克鲁德曼)中就能加以证实。
第三,这样一来,不难发现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所讲的国别“比较优势禀赋”有这样三个特征:一是成本低、积效高,如“后发展优势”(对应其劣势,是投机取巧偷懒带来惰性和违法),套利行为和思维方式(抑制创新思维);二是低门槛、高回报的外部性优势,如以最大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搭便车”+“承诺扯皮”;三是在现行规则中发挥中国人固有的病毒性“谋略优势”(逾矩思维)和“体制性欺弱侵权优势”(官本位主体思维)。
最重要的是,大概因为林先生知晓“胜之不武”的道理,他有意无意地只讲“后发展优势”(套利思维)和“谋略优势”(逾矩思维),搁置“外部性优势”和忽略“体制性欺弱侵权优势”(官本位主体思维)。而套利思维、逾矩思维,如“田忌赛马”,出其不意地拿自己的长项比别人的弱项,属于典型的“聪明之恶”——不守诚信、破坏游戏规则(如破坏奥运会拳击、摔跤、举重、田径等项目对等比赛规则),而(官本位)强者通吃的主体思维,导致中国式“资源垄断+半管制半市场+强拆”大行其道。结果在理论上回避或遮盖了中国“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空前激化这一事实真相。
第四,中国社会现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是否与产业和技术对应?其上层建筑是否内生于经济基础?或者说,中国现行包括官本位的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税收、媒介制度安排及其双轨渐进改革,是否内生于与中国现行包括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对应的产业和技术?也就是两者之间是否相适应以及相互作用、随时间变化的结果情况如何?19大报告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背后,是否与“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之间的基本矛盾”有关?很显然,在“基本矛盾”作用下,各级政府及国企唯一可能用得上的法宝,就是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对这片国土、人民等一切资源实行绑架性和毁灭性的“全面负债经营”。只要是为了发展,为了GDP增长,中国官员就敢于让中国社会、环境、国家、国民及其子孙付任何代价,因为,中国官员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三个硬道理”+“三大优势禀赋”。三个硬道理是:第一个是部门、行业所属的所谓“国有制”,第二个是GDP政绩考核标准,第三是习惯性抑制社会组织创新(甚至抑制政府组织创新);三大优势禀赋是:资源不对称优势、信息不对称优势、权责不对称优势。这既是中国政府(官员)的比较优势,也使其陷入“萧何等式定律”(参看《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8年第38期)。所以,凡在中国讲比较优势,都必须弄清是:谁的比较优势?谁主导了要素禀赋结构方式?双轨渐进式改革的比较优势,是政府干预力,还是企业自生能力?从双轨渐进改革看,要素禀赋结构,如果仅仅是指“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及产业、技术水平”,而不包括“官本位的土地财政、金融、税收、媒介制度安排”,那么显然是不完全概括。而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涉及“基本国情”或“中国特色”的评估。
第五,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自然也就不讲“后发优/劣二重性”(参看杨小凯与林毅夫2002辩论),而只讲“后发优势”,也不讲“产业规划能效/能耗二重性”(参看林毅夫与张维迎2016辩论),而只讲“产业规划的有效性必要性”,而不及其余。这在当今世界出现“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而各国公民个体和共同体生命自组织内生性活力与外连接平衡能力日益强化,普惠配置资源生态化时代(相对殖民时代、自由贸易时代)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条件下,重新强调发展主义的主权国别斗争必要性,从而让本国公民、社会作“牺牲”的秦皇汉武式谋略思维,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违背了普遍寓于特殊之中的常理,更失去“作大GDP蛋糕”的目标和方向。
第六,于是,我们也就很难看到“新结构经济学”在“区域比较研究、地域比较研究(含横向国别比较)、城乡市农比较研究,特别是社会阶层比较研究”方面,提出富有理论创新的方法和政策措施。因而,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也就整体上忽略了这片土地上每个有基本感知能力和常识的人,都很容易发现的资源性背负失衡——自然背负失衡、社会背负失衡、家庭背负失衡(身心灵亚健康)等——广义生态背负失衡这一经验事实。
我想说明一下,具有这些理论缺失和结构性遗漏的经济学理论,远不只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也包括林毅夫先生要引入的结构主义,以及与之划清界限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华盛顿共识’政策药方”,甚至包括以“市场经济理论3.0”相标榜的所谓“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顺便说一句,有人为了解释“中国奇迹”,将“市场经济理论”划分为1.0、2.0、3.0三个类型——即:从斯密以来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属于市场经济理论的1.0;以凯恩斯、以及更早的李斯特为代表的提倡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属于市场经济2.0;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市场经济3.0——并且认为,市场经济理论3.0是对2.0的继承和发展,并与市场经济理论1.0根本对立。
乍一看,这种划分,似乎突出了市场经济3.0在“三维主体市场经济理论”中的经济学地位,而且,把政治、政府(国家)、上层建筑对经济、企业、基础的反作用乃至超级能动作用嵌入到传统经济学之中。
但是,非但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或“涨价去库存、增产降产能”“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局面,反而会加剧“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以及“公民、社会边缘化”趋势(“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既可以办大好事,也可能办大坏事!),乃至“社会底座”坍塌(乡村败落或者城市空心化)和“自然报复”的问题——即反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
只要没有跳出“政府经济”“市场经济”二元经济形态,以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二分法这种单纯经济学思维方式,“让生产回归生活”——即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地休养生息——当代经济学,就不能走出“世纪钟摆”的尴尬局面。换句话说,正如当年“单纯军事观点”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一样,今天,“单纯经济学思维”也不能解决中国经济以生态文明建设观之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问题。
基于此,“新结构经济学”有没有“在更一般的理论意义上讲清楚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边界,并且可以为更新颖的经济学思路提供基础”的潜力,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但我想,无论“新结构经济学”是否有这样的潜力,我都祝愿林毅夫先生凭借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南南合作研究院的平台,“培养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把中国学子带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良好愿望,可望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最后,林毅夫先生对建设都江堰的李冰父子的那份虔诚,让我再次肃然起敬。我也对林先生喜欢王阳明哲学,十分好奇。由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就是力量,管理就是力量,权力就是力量,资本就是力量,得到广泛普及,因而近年出现了“良知教”、“阳明热”、“四句教”、“良知教育”、“阳明学院”现象,就可以理解。
但是,谁的心里都知道的一个常识是:知识、科技没有方向,知识、科技也“不是一块印好的硬币,可以拿来就用”(培根),必须经过个体生命自组织。而管理、权力、资本有力量,也有自己的方向,可管理、权力、资本的方向,指向邪恶(操纵、垄断)的概率远远大于指向正当适宜(公义、均衡),至少是具有“两可性”。
这是因为,在社会分工意义上,知识、科技属于信息能量范畴,是非独占性工具使用价值,而管理、权力、资本属于物质能量范畴,是可独占性工具,因而具有价值倾向。当代中国盛行各式各样“知行合一”“知成一体”的“成功学”,然而“缺德”咋办?Impropriety咋办?这也是亚当·斯密1759年发表《道德情操论》时面对的首要问题,正因为如此,他迟至15年后才惴惴不安地发表了《国富论》。(2018年1月26日于复旦望道苑38101A开关居)
我一直坚信,中美贸易代表团,有智慧达成旨在促进结构性改变的贸易协定。如此,以上梳理工作,将可能对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打开思路。
公陽子2019年5月3日於深圳羅湖大酒店
作者:錢 宏(全球共生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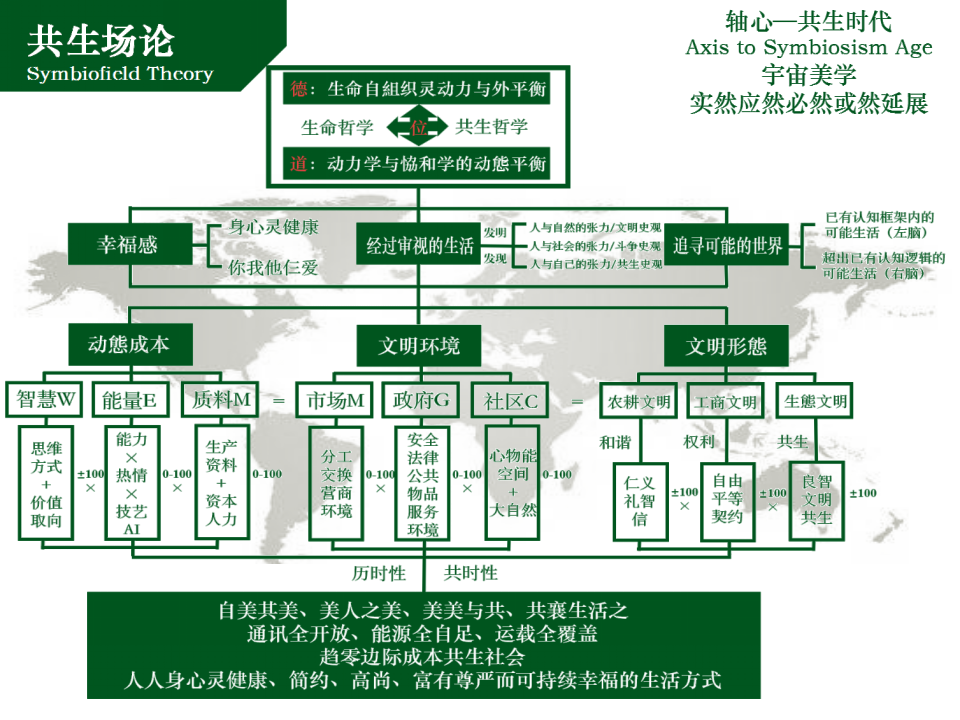





您好!请登录
已有0评论
购物盒子